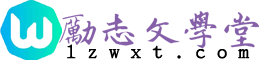巴金:窗下
巴金:窗下

敏,我現在又嘮嘮叨叨地給你寫信了。我到了這個城市已經有兩個多月。這中間我給你寫了五封信。可是並沒有收到一個字的迴音。難道你把我忘記了?還是你遇到了別的意外事情?你固然很忙,但是無論如何你得給我一封回信,哪怕是幾個字也可以。再不然就託一個朋友傳幾句話。你不能就這樣渺無音信地丟開了我,讓我孤零零地住在這個陌生的大城市裏。你知道我有着怎樣的性情,你知道這樣一種生活在我的精神上會產生什麼樣的影響,那麼你爲什麼默默地讓我受這些折磨呢?
我還記得兩個多月前我離開你的時候,月臺上人聲嘈雜,我們躲在車廂的一角,埋着頭低聲談話,直到火車快開動了,你才匆匆地走下去。你在車窗下對我笑了笑,又一揮手,就被火車拋在後面了。你不曾追上來多看我幾眼,我也沒有把頭伸出窗外。我只是埋着頭默默地回想你剛纔說的那幾句話:“到了那裏,你也許會感到寂寞。你要好好地照應你自己。你也該學會忍耐。……我就怕你那個脾氣,你激動的時候,連什麼事情都不顧了!……”
你看,現在我也能夠忍耐了。我居然在這個陌生的地方,在這個寂寞的房間裏住了兩個多月,而且不知道以後還要住多久。這其間我也曾起過沖動,但是我始終依照你的勸告,把它們一一地壓下去了。這些時候我很少到外面去。每天我就坐在一張破舊的寫字檯前,翻讀我帶在身邊的幾本舊書,和當天的報紙。等到我的腰有些痠痛了,我才站起來,在房裏默默地踱一會兒。這樣的生活有時連我自己也覺得單調可怕,我的心漸漸地像被火烤似的痛起來。我昂起頭大大地吐了一口氣。我跨着大步正要走出房門,但是你的話忽然又在我的耳邊響了。我便屈服似的回到寫字檯前,默默地坐下,繼續翻讀書報。直到朋友家的孃姨給我送晚飯來,我才明白這一天又平淡地過去了。
我常常坐在窗前給你寫信。我覺得最寂寞的時候或者火在我心裏燃燒起來的時候,我就給你寫信。我的寫字檯放在窗前,窗臺很低,我一側頭便可以看見窗外的景物。上面是一段天空,藍天下是土紅色的屋頂,淡黃色的牆壁,紅色的門,牆壁上一株牽牛藤沿着玻璃窗直爬到露臺上面。門前有一條清潔幽靜的巷子。其實這對面的房屋跟我住的弄堂中間還隔了一堵矮牆。越過這堵矮牆纔是我的窗下。從我住處的後門出去,也有一條巷子,但是它比矮牆那面的巷子窄狹而污穢,牆邊有時還積着污水和腐爛的果皮、蔬菜。
這一帶的街道本來就不熱鬧,近幾天來,經過一次集團搬家指當時這一帶的居民從虹口地區搬進“租界”裏的事情。以後更清靜了。白天還有遠處的市聲送來,街中也有車輛駛過,但是聲音都不十分響亮。一入了夜,一切都似乎進了睡鄉。只偶爾有一輛載重的兵車指日本海軍陸戰隊的鐵甲車。日本海軍陸戰隊的兵營就在這附近。隆隆地駛過,或者一個小孩的哭聲打破了夜的沉寂。平常傍晚時分總有幾個鄰家的小孩帶着笑聲在我的窗下跑過,或者就在前面弄堂裏遊戲,他們的清脆的、柔和的笑聲不時飛進我的房裏。那時我就會凝神地傾聽他們的聲音。我想從那些聲音裏分辨出每個小孩的面貌,要在我的腦子裏繪出一幅一幅的圖畫,彷彿我自己就置身在這些畫圖中而忘了我這個寂寞冷靜的房間。
如今連這些笑聲也沒有了。這幾天裏面我的周圍似乎驟然少去了許多人。這周圍的生活也起了改變。甚至那個說着古怪的方言的孃姨送飯來時也帶着嚴肅而緊張的面容,吃力地向我報告一些消息。我似懂非懂地把她的話全吞下了。其實報紙上載的比她說的更清楚。
這裏一個多月沒有下雨,一連幾個晚上月色都很好。敏,你知道我是喜歡月夜的。倘使在前幾個月,我一定會跑到外面去,在街上走走,或者到一個清靜的地方坐坐。但是現在我卻沒有這種心思。而且外面全是些陌生的街道,我又沒有一個可以和我同去散步的朋友。所以我依舊默默地坐在寫字檯前面,望着攤開的書本。時間偷偷地從開着的窗戶飛出去,我一點兒也不曾覺得。只有空氣是愈來愈靜,愈涼了。
“玲子,玲子。”下面忽然起了一個男人的輕微的喚聲。
我驚訝地掉頭往窗外看去。我的眼前一陣清亮。越過矮牆,那條水門汀的巷子靜靜地躺在月光下面。一個黑影撲在門上。
聲音是我熟悉的,影子也是我熟悉的。穿着灰布長衫的青年男子到這個地方來,並不是第一次。
“玲子,玲子。”那個年輕人用了戰抖而急促的聲音繼續喚着。他走下臺階到牆邊踮起腳輕輕地叩玻璃窗。
房裏有了聲音,窗戶呀的一聲開了半扇,一個黑髮蓬鬆的頭探出來,接着是女人的聲音着急地說: “你——你,我叫你晚上不要來。外面情形不好,你怎麼又跑來了?”
“你開開門,出來,我跟你說幾句話。”男人催促道,他的聲音裏含了一點喜悅,好像他看見少女的面貌,心裏得到一點安慰似的。
“你快說,快說!你快點走,會給我爹碰見的!”女的不去開門,卻把頭往外面伸出來些,仍然帶着畏怯的聲音說話。一陣微風吹過,牽牛藤跟着風飄舞。幾片綠葉拂到她的濃髮上。
“你快點出來說。我說完就走,不會給你爹看見的。”男人固執地央求道。
少女把頭縮回去關上了窗戶,很快地就開了門出來,站在門檻上。男人看見她,馬上撲過去抓起她的一隻膀子。
她把身子一扭掙開了,也不說什麼抱怨的話,卻只顧催促道:“你快說!快說!我爹跟東家〖ZW(〗她的東家是日本人。就要回來了。”
“你爲什麼怕見我?難道你真的相信你爹的話?”男人驚疑地說,他輕輕地乾咳了兩聲。
“你不要故意說話來氣我。我怕我爹會碰見你。我爹要曉得你還常常來,他定規要想方法對付你。”少女膽怯地答道。男人還沒有答話,她又關心地接着說:“這樣晚你還跑來做什麼?你的身體不好,你又在咳嗽。”
少女依舊站在門檻上,男人背靠在門前牆邊。等她閉了口他便氣憤地說:“這個我倒不怕。你爹太豈有此理。從前我們在鄉下的時候,他待我很好。那時我們在一起,他沒有說過一句話。現在他在你東家這裏很得意,就連我的面也不要見了。其實我在小學堂裏教書,掙來的錢也可以養活自己,就跟他女兒來往,也不算坍他的臺。況且他的行爲就不是什麼高尚的。“
少女伸過手去把他的一隻手捏住,溫和地說:“我爹是個糊塗人。他只聽東家的話,東家說什麼好,就是什麼好。我爹說你們是壞人,說你們專教小孩子反對‘友邦’反對“友邦”,指抗日。,又說你們鼓勵小學生抗這抗那的。”
“這一定是你東家的意思。你爹真是個漢奸!”男人擺脫了少女的手氣沖沖地插嘴說。“你難道也相信我是個壞人?”
少女望着男人憂戚地微笑了,她溫柔地答道:“我當然不跟他一般見識。我相信你是好人。不過我爹完全跟着東家一鼻孔出氣。他說過他看見你領着小學生遊行,喊口號。他恨你,他說你是個亂黨。你跑到此地來看我,很危險。我很不放心。”
“我不怕。我不相信他敢害我!”男人依舊氣惱地說,他接連乾咳了幾聲。他把一隻手按住胸膛,喘了兩口氣。
“你看,你的病還沒有好,你又要生氣!你也要好好地養息養息。你還在吃藥嗎?”少女憐惜地說。
“近來倒好一點。好些時候不吐血了。咳嗽也不多。我想大概不要緊。”男人溫和地答道。 “我看你千萬不可大意。你也應該當心。現在不早了,你還是回去吧。”少女關心地勸道。 這時候,從巷子的另一頭送過來皮鞋的聲音,在靜夜裏聽起來非常響亮。
“好,玲子,我走了。”男人慌張地說,就伸手去握住玲子的一隻手,不立刻放開,一面還繼續說:“我也就因爲這兩天外面謠言很多,我很擔心你,才特地跑來看看。你要早早打定主意。你從你爹那裏聽到什麼消息嗎?”
少女微微地搖頭,回答道:“我爹什麼話也沒對我說。他整天跟東家在外面跑。他從來不給我講那些話。你不要擔心我。這兩天情形不好,你自己跑到此地來,倒要當心在半路上出毛病,冤枉吃官司……”她沒有把話說完,遠遠地響起了汽車的喇叭聲。她連忙掙脫手,急急說:“你快走,東家回來了。”
“玲子,我走了,明天晚上再來看你。”男人下了決心似的說,就轉過身朝外面大步走去。 “明天晚上你不要來。”玲子還跑下石階揮手囑咐道。但是他好像沒有聽見似的連頭也不回就走出去了。
少女還在門前牆邊站了一會兒。她倚着牆仰起頭看天空。清冷的月光沒遮攔地照在她的臉上,風把她的飄蓬的濃髮吹得微微飄舞。她的並不美麗的圓臉這時突然顯得十分明亮了。那一對不大不小的眼睛裏充滿着月光。我靜靜地注目看,我不能夠看見她的黑眼珠。原來眼眶裏包了汪汪的淚水。
並沒有汽車開進巷子裏來,喇叭聲早消失在遠方了。少女方纔的推測顯然是錯誤的。這個清靜的巷子比在任何時候都更靜。地上是銀白色的。紅色的門,淺黃色的牆,配上她那身白底藍條子布的衫褲。在玻璃窗旁邊還有一株牽牛藤在晚風裏微微舞動它的柔軟的腰肢。這是一幅靜的、美麗的、幻想的圖畫。我不覺癡癡地望着它。我忘了我的房間。我覺得我是在另外一個世界裏面了。
少女忽然猛省似的嘆了一口氣,便走上石階,推開門進去了。深紅色的木門關住了裏面的一切。牆壁上的牽牛藤依舊臨風舞動,而且時時發出輕微的嘆息。
空氣愈來愈靜,而且愈涼了。房間裏漸漸地生了寒氣,我的背上忽然冷起來。遠遠地響起了火車頭的叫聲。接着就是那喘氣似的車輪的響動。我知道我這一天坐了夠多的時候了,便站起來闔上書,伸了一個懶腰。就在這個時候一輛汽車駛進水門汀的巷子裏來。車子在牽牛藤旁邊停住。汽車伕下來打開車門,一個豔裝的中年婦人,和兩個中年男人從車上出來。三個人都穿西裝,我認得他們的面貌。汽車往外面開走了。
“玲子!玲子!”那個圓臉無須的胖子大聲叫道。他伸出手在門上捶了幾下。這個人就是玲子的父親。玲子在房裏答應着,開了門。她的父親恭敬地彎着腰讓東家夫婦走進裏面,然後跟着進去。門又緊緊地關上了。他們在房裏大聲談話,說的全是異邦的語言異邦的語言:指日本語。。我不明白他們在講些什麼。
敏,我告訴你,玲子和她的父親,還有小學教員,還有東家夫婦,這些人我都熟悉。我並不曾跟他們談過一句話。但是我這兩扇窗戶告訴了我種種的事情。倘使我的小小的房間就是我的世界,那麼除了我的兩三個朋友外,他們便是我的世界中的主要人物了。他們每天在我的眼前經過,給我的靜靜的世界添了一些點綴。所以他們的言語和行動會深深地印在我這個漸漸變遲鈍了的腦子裏。
小學教員第一次到這裏來是在一個黃昏。那個時候我還不知道他的職業。玲子的父親一早就出去了。東家是下午回家以後又帶着太太一道坐汽車出去的。玲子站在門前。這一家就只有她一個人。東家夫婦似乎沒有小孩,也沒有別的親人。他們去了不多久,玲子正在窗下伸手到牽牛藤上去摘那剛剛開放的紫色花朵。一個人影輕輕地飄到她的身邊。接着是一個欣喜的喚聲:“玲子!”
我看見那個天真的少女掉過頭,滿臉喜色地接連說:“你——你!”
“你看,我果然來了。我答應你,我決不失信。”男人得意地說。
玲子不說什麼話。她把身子倚在牽牛藤上,夢幻似的打量他。
“玲子,你老看我做什麼?你難道還認不得我?”男人微笑地說。
玲子的圓圓臉上露出天真的微笑。她說:“我看你氣色好多了。”
近來我自己也覺得好多了。”男子笑答道。他把聲音壓低了問:“你爹跟你東家一道出去的嗎?他們什麼時候回來?”
“我爹先出去。他們今天最早也要十一二點鐘纔回來。你多坐坐,不會碰見他們。”玲子低聲回答。
“玲子,我說,我——我看你還是早點打定注意,在此地做事情終歸不是好事,”男人說話的聲音更低了些。但是我那注意傾聽的耳朵還能夠抓住話的大意。“你那個東家不是正當的商人。你爹簡直是個……”我想他接着一定會說出“漢奸”一類的字眼,但是他突然換了另外的幾個字:“他簡直忘了本了。”
“你當心點,不要瞎說,會給人聽見的。”玲子變了臉色驚懼地阻止道。她又皺起眉頭憂鬱地說:“我爹決不肯放我走的,我有什麼辦法?我也明白在此地做事情不好。東家不是個好東家。他們那種古怪脾氣也叫人夠受。可是我爹說過他將來還要帶我到東家那邊去。我真有點害怕……”
男人着急起來,他忽然揚起聲音說:“那麼你還癡心跟着你爹做什麼?我害怕他將來真會帶你到那邊去,他會入那邊的籍做那邊的人。難道你肯跟着他去當——?”他似乎要說出先前突然嚥住了的那兩個字,可是一陣皮鞋的聲音打岔了他。三個混血種的青年男女帶笑地說着英國話走過來。
“我們進去坐坐。”少女看見人來,吃了一驚,就輕輕地拉了一下男人的衣袖,兩人走上石階推開門進去了。深紅色的木門關住了他們的影子。
我依舊坐在窗前。寫字檯上的書和別的東西漸漸地隱入陰暗裏去了。我並不想看見燈光。我讓電燈泡板着它的冷麪孔。我把身子俯在窗臺上,靜靜地望着下面清靜的巷子。空氣似乎凝固不動,讓黃昏慢慢地化入了夜。燈光從那個房間的玻璃窗裏射出來。我聽不見講話聲。但是突然從鄰近的房間裏響起了西方女性的歌聲,有人在開無線電收音機了。
過了好些時候,紅色的木門開了,一個影子閃出來,就是那個男人。被稱爲“玲子”的少女也在門檻上出現了。男人急急地往外面走去。玲子卻倚着門框默默地望着他的背影。
那個男人以後還來過兩次。有一次是在早晨。玲子的父親和男東家剛出門不久,女東家似乎還在睡覺。男人匆忙地在隔壁門前跟玲子耳語片刻,便走了。
另一次還是在傍晚,那個男人來了以後,他們兩個在門前談了半個多鐘頭。從這次的談話我才知道男人在小學校裏教書,他患着肺病,而且在這個都市裏沒有一個親人;我也知道一點玲子的父親和東家的關係。
以後許多天都沒有看見那個男人的影子。玲子有時候也出去。我見過兩次她急急地從外面走回來,都是在傍晚。其實也許還不止這兩次。我的眼睛有時候也會看漏的。
這個人家還有一個孃姨。不過每天晚飯後我就看見她回家去。有時她白天也似乎不在這裏。究竟她是在怎樣的條件下被僱用的。我的眼睛和耳朵卻不能夠幫忙我探聽了。
男東家永遠板着面孔,在鼻子下面留着一撮黑鬍子,短胖的身子上穿着整齊的西裝。女東家永遠是濃妝豔服,連頸項上也抹了那麼厚的白粉。那個圓臉無須的玲子的父親永遠帶着諂諛的微笑。
有一次在晚上玲子的父親一個人先回來了。這一對父女起初平靜地在樓上房間裏談話。後來我就聽見了玲子的哭聲和她父親的罵聲。我聽不出來他們爲了什麼事情在爭吵。他們好像在講那個小學教員的事,又似乎在講別的事。我彷彿聽見他厲聲說,不許她再到什麼地方去。
這哭聲和罵聲並沒有繼續多久,後來父親和女兒似乎又和解了。樓上露臺前兩扇玻璃門緊緊閉着。玻璃上蓋着花布窗帷。此外我的眼睛就看不見什麼了。
但是第二天夜裏八點鐘光景,玲子一個人悄悄地跑出去了。大約過了一個鐘頭,我纔看見她站在石階上摸出鑰匙開門。水似的月光軟軟地衝洗着她那苗條的身子。
再過一天那個小學教員來了,就是我在前面提到的他敲着玻璃窗低聲喚“玲子”的那一次。 敏,你看,我現在變得多了。這些事情在從前我決不會注意。但是現在我卻這麼貪婪地想知道它們。而且我可以靜靜地在窗前站或者坐幾個鐘頭,忘掉了自己。而活在別人的瑣碎的悲歡裏面。你看,我真的學會忍耐了。我居然冷靜地伏在案頭寫了這麼長的信,告訴你這些瑣碎的事情。我爲什麼要拿這些來耽誤你的繁忙的工作呢?
敏,我是告訴你:我已經學會忍耐了,我已經學會忍耐了!忍耐了!忍耐了! “今天聽說外面情形很不好,住在這一帶的人都往別處搬,你還跑到此地來?你膽子真大!”又是玲子的聲音。
“有你在此地,我怎麼放得下心!外面情形真的不好,不一定全是謠言。你應該早早打定主意,”小學教員焦慮地說。
這是在傍晚,兩個東家都出去了。玲子一個人在家裏。這天從早晨起就看不見太陽。天空帶着愁眉苦臉的樣子。憂鬱的暗灰色的雲愈積愈多,像要落雨,但始終不見落下一滴淚水。空氣沉重,也沒有一點風。在我這邊隔壁人家連牀也搬走了。孃姨送晚飯時來告訴我,鄰近幾家的主人昨晚都在旅館裏睡覺。我還不大瞭解她的方言,但是我懂得大意。
“女東家要回那邊去了。爹一定要我跟她去。你說我還打什麼主意?”玲子的苦惱的聲音不高,但是我已經聽清楚了。我掉頭去看下面的巷子。玲子站在牽牛藤旁邊。男人挨着窗臺。
“你跟她去?你爲什麼要跟她去?你又不是把身子賣給他們的!”男人氣憤地說,但是聲音也不高。話剛完,他咳了兩聲嗽。
玲子關心地望了他半晌,才膽怯地說:“我爹跟他們商量好的。東家說此地不能住下去了,中國人壞得很,萬一打起仗來會亂殺人。女東家怕得很,她不肯在此地住下去。她就要回到他們那邊去。我爹也說一定要打仗。中國人打不贏,自然就會亂來。……”
“難道你爹就不是中國人?玲子,你是明白的,你一定不會相信他這種話,……”男人似乎咬牙切齒地說。這時候一種火似的情感猛然從我的心底冒上來。我的注意滑開了。我聽漏了幾個重要的字,我只得用黑點代替他們。等到我再用心去聽他們談話時,送進我耳裏來的就只是一陣被壓抑住的乾咳。 “你剛剛好一點,又生氣了,咳起來也怪難受的。”她的聲音裏交織着好幾種情感,連我的心也被打動了。
“玲子,你得馬上打定主意跟我走。你跟你女東家到那邊去,不會有好處,你跟着你爹那種人過日子,不會有好處,不過白白害了你自己,”男人半勸告半央求地說。他把身子從窗臺移開,挨近她,差不多就在她的耳邊說話。
“你——你怎麼辦?”玲子埋着頭不回答,卻關切地問。
“我?我也是一箇中國人。我怎麼辦?你問你東家,你問你爹,他們知道的!”男人忽然提高聲音答道。
“你小聲點,會給人聽見的。我怕,我怕得很。你說真的會打仗嗎?”玲子略略抓住男人的膀子,驚惶地低聲問。
“你還是問你爹,問你東家吧。他們比我更知道。”男人生氣似的答道,然後又換了語調問:“你女東家幾時動身?”
“我不曉得。多半還要等幾天。他們做事總是鬼鬼祟祟的。我真不要到那邊去!可是我又怕我爹。”
“你怕他做什麼?有我在。你打定主意明天就逃到我那裏去,你跟我走!”男人的後面兩句話是用很輕的聲音說出來的。我沒有把字眼聽準。但是我猜到了那個意思。
“我怕我爹他會害……”玲子遲疑了一下,就用了同嗚咽相似的聲音說。但是剛說到“害”字,她忽然變了臉色,好像看見了什麼可怕的東西似的,一把推開男人,慌張地急急說:“東家回來了,你快走。下回來吧。”
男人吃驚地回頭一看,連忙說了一句:“我明晚再來。”就轉身往外面走去,這時玲子已經跑上了石階。
女東家捧了許多紙包坐着人力車回來了。玲子推開門,又把紙包接過來,等着主人下車,然後跟着往房裏去了。
樓下房裏有了燈光。然後樓上房裏也有了燈光。露臺前的玻璃門依舊緊緊閉着。沒有人來拉起花布窗帷。
風在我的窗前吹過了。一些細小的聲音開始打破了沉悶的空氣。聲音漸漸地大起來。雨畢竟落下來了。
我關了窗戶。我不去聽外面的聲音,也不看花布窗帷。我看書,我寫信,我把我的心從窗下那條巷子裏收回來。我做我自己的事情。
但是有一件事情,我知道得很清楚:對面房間裏似乎整夜都有燈光,半夜我從睡夢中醒來時,還聽見搬東西聲,說話聲,女人的低聲哭泣,和男人的責罵。但是我太瞌睡了。 早晨,我醒得很遲。陽光燦爛地照在露臺上。牽牛藤的綠葉在微風裏顫動。我在牀上聽見牆外巷子裏汽車的聲音。等我走到窗前去看時,玲子剛剛俯下頭進汽車去。她的臉在我的眼前一晃。這匆匆的一瞥使我看清楚了少女臉上的表情。天真的微笑失去了。除了一對紅腫的眼睛外,就只有憔悴的暗黃色。
汽車很快地開走了。留下來的是孤寂的巷子。我把兩隻膀子壓在窗臺上,癡癡地望着下面。那裏並沒有什麼可看的景象。但是三個混血種的男女哼着流行的英文歌曲走過了。
藍的天空,土紅色的屋頂,淺黃色的牆壁,圍着鐵欄杆的露臺,紅色的門,這些跟平時並沒有兩樣,而且朝陽還給它們添了些光彩。一張面孔在陽光裏現出來,又一張面孔在陽光裏現出來。彷彿有兩個人站在窗前牽牛藤旁邊低聲講話。……我的眼睛花了。
“我明晚再來。”
這句話並不是對我說的,但是它卻清清楚楚地在我的耳邊響來響去。
火一般的情感忽然在我的心上升起來,好像是陽光在我的心上點了一把火似的。 敏,我又來跟你談話了。我又告訴了你許多事情。現在我似乎應該擱筆了。我爲什麼拿這些事情來打擾你呢?而且我翻看我寫好的二十張信箋,連我自己的心也被那些話攪亂了。我讀到“忍耐”,“忍耐”,“忍耐”,這些重複的字,我看到那幾個驚歎符號,我對我自己也—— 噓,一個影子在我的眼前掠過。這兩個多月來的孤寂的生活倒把我的眼睛和耳朵訓練得很銳敏了。我不用掉頭就知道那個小學教員來了。
敏,這一次你猜我怎麼辦?我還是像平日那樣連忙把頭掉過去看紅色的門和牽牛藤麼?我在前面不是明白地說過我能夠忍耐,而且我能夠冷靜地旁觀着別人的悲歡麼?
但是這一次我卻不能夠忍耐了。我聽見喚“玲子”的聲音,我突然失掉了控制自己的力量,一下子就把頭俯在寫字檯上,我不願意再看見什麼。
然而我的耳朵是能夠聽見的。他喚了幾聲“玲子”,敲了幾次玻璃窗,接着就在水門汀地上走來走去。他乾咳了幾聲,後來又去敲門。
一個人的皮鞋聲自遠而近。於是一個男人不客氣地大聲說: “沒人。通統走了。”
“我找玲子。”小學教員訥訥地說。
“給你說通統走了!今朝弗會回來!”看弄堂的巡捕粗暴地嚷起來。接着我又聽見皮鞋聲由近而遠。
“玲子。”小學教員忽然輕輕地喚了這一聲,過了半晌,他還在那裏低聲自言自語: “我知道你會跟他們走的。你太——”
我等着聽這下面的話。但是他猝然閉上嘴走了,我聽見他的窗下〖〗〖〗急促的腳步聲。
這些又是我所料不到的。
敏,我不再寫下去了。我最後還是告訴你:我不能忍耐了,我不能忍耐了!
我後悔昨天晚上爲什麼不跟着出去追他。但是現在還來得及。我要出去找他。我相信在那個小學裏一定可以把他找到。我有許多話要問他。……
1936年9月在上海 巴金寫《家》時用的桌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