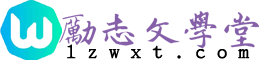街戲
常常是在街上開始。

傍晚時分,搭一程過江的車,去到漢口。隨便在某一處下車,遠遠,聽見高亢明亮的鑼鼓聲,是有人在演楚劇。
多是小街,兩邊都是居民自己蓋的房子,參差不齊,入冬家家戶戶都晾出臘魚臘肉和一掛掛的香腸;夏天,男子們當街洗澡,渾身上下只有一條短褲,水龍頭裏的冷水劈頭蓋臉地衝。如果是大街,則往往在銀行或者金融機構的門口,那裏總有一大片空地,十分寬敞,穿堂風習習而來,石獅安靜蹲坐,長髮紛披。
散淡夏夜,鑼鼓催了又催,附近的爹爹婆婆端着小板凳陸陸續續出來了。我就遠遠地站在外圍看――因爲吝嗇,不準備丟錢到飯盒裏去,帶着蹭戲的羞慚。戲班豎起兩根旗杆,掛一串大燈泡,以標誌舞臺,畫地爲牢在這裏有最明確的象徵。旦角“咿呀”一聲,一擡手,如燕之待飛,花襖花褲,都有補丁。她近了燈,我便看見上面萬年不洗的垢,而她臉上正黑汗水流着。與她配戲的小生,往往是中年人,妝化得敷衍,遮不住也沒準備遮住年紀,一把嗓子蠻粗,而她管自嬌滴滴、滴滴嬌着。這大概就是傳說中的“浪語油腔”,我是俗人,最愛聽。
戲外還有戲,旦角一下臺,身體就挺直了,她拿一個大瓷缸喝水,咕咚咕咚地,也很敬業,用袖子擋一擋臉;等待上場的丑角岔開腿坐在長凳上,玩手機,大概是在發短消息,塗了白塊的臉很專注。他們華美而破爛的衣服,浮在城市夜晚淡藍的霧裏,時空有奇怪的扭轉。而觀衆若無其事,不在乎這打成一片。
有時舞臺旁邊,會有一塊黑板,寫着劇目,《葛麻》《雙怕妻》……我都不懂。而歌的歌,舞的舞,不因爲我的無知,稍遜顏色。
我沒耐心,聽一會兒就走,很少能看到全篇。印象深的,有一部講惡婆婆的,兒媳洗好了衣服,去戶外晾,“會給人偷”,在室內晾,“沾不到陽氣”,最後惡婆婆讓兒媳把衣服頂在頭上跪在院子裏晾。兒媳遂頭頂破衣,蘇三似跪在臺中央,紋絲不動地唱着長篇大套。募地,來了一個男子,一手揭起她頭上的破衣,這一刻,多麼驚豔如同洞房,掀起你的蓋頭來――來者何人?是準備英雄救美嗎?我正浮想聯翩,原來那就是她的丈夫,惡婆婆的兒子。
楚劇無非就是這樣,說着家長裏短、婆婆媽媽。它原名黃孝花鼓,起源於清道光年間,1926年得名楚劇,流行於湖北民間。它得了名,彷彿流打鬼被封了神,是一顆地煞星,擡了身價,卻一直是地方小戲。評劇、豫劇、黃梅戲,都殺出重圍,成爲流行,楚劇卻始終無此機緣。它因此不是藝術,沒有那種端嚴的距離感。
是的,楚劇不是藝術。如果藝術是指,我必須穿上美好的吊帶裙,矜持地進入長安大戲院,端坐,優雅地在開始與結束時刻鼓掌――中間到底可不可以鼓掌?報紙上一會兒一個說法,我就像大部分可憐的觀衆一樣,被弄糊塗了,在表演當中睡着。
而藝術是否必須從肉身渡成神話,必須是“博大精深”與“霸王別姬”?可不可以,僅僅是俗世風景?
我所看到的楚劇,永遠是在街上,這麼熱鬧這麼認真,與賣鴨脖子的、炸面窩的、大聲討論家事的中年婦人一樣,就是街市自己。之於武漢,楚劇是一城呼啦啦大葉子的法國梧桐,有潑生潑長的強悍生命力。
我離開武漢後,就沒看過楚劇。楚劇會滅亡嗎?難說。老城正在大片大片地被拆除;中國人最爛熟的親戚關係,因爲獨生子女政策,向小孩們解釋起來很困難;惡婆婆們雖然是永恆的――不信請參閱搜狐婆媳論壇上那無窮無盡的“我的JP婆婆、公公、小姑子、小叔子……”等貼,但忍辱負重的好媳婦已經不多見了。
有時我想,楚劇,不是不像一個委屈求全的小媳婦的,受盡命運的侮弄,而一言不發,也許有人會來揭開她頭上的破布,也許,永遠不會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