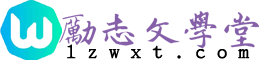飯桌·人生
我家有個小飯桌。

母親說小飯桌的年齡比她大。母親今年九十三。
母親說小飯桌是她奶奶出嫁時的嫁妝。如此算來,小飯桌已有上百年的歷史了。
母親是家裏的獨生女,是奶奶的“小當意”,小時候享受過跟奶奶在炕上用小飯桌吃小竈的待遇;母親上過幾年私塾,還在小桌上打過算盤和寫過毛筆字。
母親結婚時,奶奶看她喜歡這個小飯桌,就送給了她。小飯桌隨母親來到我們家,也有七十多年了。
我從小就記得這個小飯桌的樣子:長約1米,寬不足60公分,高30公分左右;桌面醬紫色,光滑如鏡;四條“老虎腿”,敦實健壯;渾身卯榫結構,不見一個釘子,做工精細,棱角光滑。小飯桌小巧玲瓏,似一個工藝品。小飯桌到了我們家,我不曾記得在上面吃過幾次飯。桌子太小,屬於那種小炕桌,適合於少數人坐炕上吃飯用。所以那時只有過年,一家人才擠在炕上用小飯桌吃飯,平時一般在地下,圍着一張大桌子吃飯。再就是家裏來了客人,父親陪客人在炕上用小桌吃飯。
從我記事起,我們家就是一個八口人組成的大家庭,父母和我們弟兄姊妹六個。不忘一大家子人圍着大桌子一起吃飯的情景:父親坐桌子這邊,對面是大哥,二哥挨着父親,對面是大姐,我和弟弟坐一頭,母親和小妹坐另一頭。母親吃飯時經常缺席,一會兒去拿碗筷,一會兒又去給我們盛飯,安安穩穩坐着吃頓飯的遭數不多,常常是我們都吃完了,母親一邊拾掇桌子,一邊隨便對付幾口。母親總是忙碌,有幹不完的營生。
說實話,那時飯桌上不像現在七碟八碗的這麼豐盛,飯菜單一簡單,“地瓜餅子,鹹菜羹子”是家常便飯。很多時候飯桌上沒有菜,只有一個鹹菜碗,裏面盛的是鹹蘿蔔、鹹菜疙瘩、蝦醬,好一點的是小魚乾;飯就更簡單了,一年裏,有大半時間飯桌上放一笊籬盤子地瓜和餅子,每年從秋天鮮地瓜一下來,能一直吃到來年的春天;鮮地瓜吃完了,飯桌上就換上了一盆或一鉢子地瓜絲,每人手裏一個碗,涼水泡着地瓜絲,能吃上玉米麪粥泡地瓜絲,算是改善生活。那時玉米餅子是好的,豆麪餅子(即玉米麪裏摻些豆麪)更好,更多的是玉米麪裏摻上地瓜餷子。餅子是好的,可不能隨便吃,只有父親和下地幹活的哥哥,一頓才能吃上一個囫圇餅子,我和弟妹,還有姐,只能兩人或三人吃一個,很少看到母親吃餅子。有時母親拿起一塊餅子,吃上一兩口,又給了我和弟妹,說她不喜歡吃餅子。其實我心裏很清楚,母親不是不喜歡吃,而是捨不得吃。
過年了,小飯桌派上了用場,三十中午,一家人圍着小桌坐炕上吃飯,小桌上魚啊、肉啊、雞啊、鴨啊……擺得滿滿當當,白麪餑餑、大米管夠,這是一年中最豐盛的午餐;除夕夜,一家人吃團圓餃子,還是在炕上用小桌;送走了年,又恢復了正常,一家人坐地下用大飯桌吃飯,桌上的飯菜也恢復了原樣。
從那時起,我就好像覺得小飯桌只適合用來吃美味佳餚,趟過貧窮,走向富裕,是幸福生活的象徵。
我多麼希望能坐在小飯桌旁吃飯啊!
有件事,我終生難忘。這天,我們家管學校老師的飯。那時村裏學校的老師,多是本村民辦的,只有幾個公辦的。民辦老師都是掙工分,在自家吃放;公辦老師拿工資,在全村學生家派飯吃。儘管當時老百姓的生活還很苦,可再苦也不能苦了老師,不管老師派到誰家吃飯,都是好菜好飯地伺候。老師到我家吃飯這天,中午母親爲老師烙了油餅,也叫“千層餅”,還炒了大白菜。父親陪老師在炕上用小桌吃飯,父親吃得有些斯文,卻不停地勸老師搛菜、吃餅,老師一邊吃,一邊說:不客氣,不客氣。這時,我趴在門框上,看着老師那張油光發亮、不停咀嚼的嘴,饞得我直咽口水。一定是我的饞相打動了老師,他把我叫到跟前,撕了一塊油餅給我,我狼吞虎嚥地吃起來。父親喊我一句:這熊孩子,快出去!母親走過來,一把把我拽出,用手擰我嘴巴,小聲說:就你這小嘴饞!母親下手有點重,我感到很痛,可沒敢發出聲響,硬是穩穩地把餅吞下,真好吃……
從這時起,我就暗下決心:將來當一名老師,吃派飯!當爹也挺好,能陪客人吃客飯!
後來,我發現了一個問題:父親雖然能陪客人吃飯,可好像每頓都沒吃飽,客人一走,小飯桌一撤,父親總要再吃些我們吃的飯。我終於明白:父親說是陪客人吃飯,還那麼斯文,完全是出於禮節,做做樣子罷了,並不真吃。
多少年過去了,我未能如願以償地成爲一名教師,可吃飯早就達到了吃派飯的水平,千層餅已成爲家常便飯;我也成了一名父親,無數次陪客人在家裏或飯店吃飯,可從來沒有像父親那樣只陪不吃。
多少年以後,母親一直不忘當年擰我嘴巴之事,甚至感到愧疚,後來我每次回家,都給我烙千層餅,我又吃又拿。
母親烙的千層餅,稱得上是一絕:說是千層,怕是達不到,可層層疊疊,足有十幾層厚,且層薄如紙,每層之間夾有油鹽蔥花,鹹淡適中,外脆內柔,美味至極。烙千層餅講究的是火候,可最重要的是“摔餅”,即餅烙到一定火候,將餅在鍋裏反覆地摔,越摔餅越層次分明,越摔餅越鬆軟可口。
母親摔餅的樣子記憶猶新:人站鍋臺邊,先用鏟子從鍋裏剷出一張餅,然後用另一隻手託着,在眼前迅疾完成一個翻轉,用力把餅摔進鍋裏,只聽“嘭”地一聲響……隨着“嘭嘭”響聲不斷,油餅就發出誘人的香味……
儘管母親年事已高,可我每次回家,她仍爲我烙千層餅;餅烙好了,再做幾個菜,端上炕,放小飯桌上,我和父親喝酒,母親有時也喝一小杯,小屋充滿溫馨……
還是這間屋子,還是這張小桌,還是母親烙的千層餅,時光彷彿倒流,又回到了過去,當年趴門框上看老師吃餅的我,現在倒像是吃派飯的老師,陪我的是父母。父親吃得很自如,沒當年那麼斯文,母親儼然是個陪客的,不停地勸我多吃、給我搛菜,嘴裏還唸叨着:摔不動了,摔不出張好餅了!
母親在千方百計彌補過去,恨不得把缺失的都補回來;我在努力尋找着那遺失的千層餅的味道……
我們家的飯桌換了好幾個,但那個小飯桌卻永久地保留了下來。當我們兄弟姊妹都像離巢的鳥兒一樣離開老家,遠離父母,父母便在炕上用小桌就餐,吃完飯也不拿下,就放炕頭上,上面放着茶壺和杯子,一張小桌,兩位老人,親密無間,相依相伴……
母親曾說過,她奶奶曾找算命先生給她算過命,說她這輩子是“脖錘子”(古時的紡錘)命——兩頭粗中間細,就是說小時候和老了能享福,中間要吃苦遭罪。母親說她就是這命,小時候沾了獨生女的光,跟着奶奶吃過小竈,也算沒遭多少罪,還讀了幾年私塾,能寫會算,還喜歡唱歌,本來是有機會走出去的,可由於家人的反對和阻攔,只好“裹足不前”。母親說,抗戰期間,她們村進駐八路軍的“魯迅劇團”,家裏住着幾個男女演員,母親跟他們打得火熱,劇團離村時,他們勸母親參加劇團,隨劇團一起走,母親也有意,可奶奶和父母堅決反對,怕她真的跟劇團走了,就把她鎖在屋子裏。劇團走了,母親留下了,後來跟我父親結了婚,從此過上了平凡的日子……
前些年母親常常爲此事感嘆:當初我要是跟着劇團走,說不定就成了一名演員,也算是老革命了!隨着年歲增高,近些年很少聽到母親這樣的感嘆,倒是常唸叨:人啊,只要平平安安一輩子,比什麼都強!
回顧母親的一生,母親很平凡,不過是一個普普通通的家庭婦女,用母親自己的話說是:“打了一輩子‘鍋臺轉’,跟飯桌子算計了一輩子!”
算命先生說母親是“脖錘子”命,我倒覺得母親的一生跟飯桌更親近,母親把一生的精力都用在豐富我家的飯桌上,爲了能讓一家人吃飽吃好,她卻吃盡了苦頭。如果沒有母親一輩子圍着鍋臺轉和跟飯桌的算計,能有我們的今天嗎?
“民以食爲天”。我覺得沒有比吃飯對生命更重要的事情了,沒有比飯菜跟飯桌再親密的關係了。所以,飯桌與人生有着密不可分的關係。
我時常想,無論是母親當年邁出了那一步,走上文藝舞臺,圍着舞臺轉,還是未邁出這一步,走進農家小院,圍着鍋臺轉,母親都是人生舞臺上的主角和強者!母親老了,該享享清福了!母親平凡而偉大,願母親長命百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