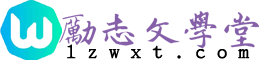名家好的文章摘抄及賞析學生
名家好的文章摘抄及賞析學生

導語:這裏本站的小編爲大家整理了三篇名家好的文章摘抄及賞析學生,希望你們喜歡。

一、《貓》夏丏尊
白馬湖新居落成,把家眷遷回故鄉的後數日,妹就攜了四歲的外甥女,由二十里外的夫家僱船來訪。自從母親死後,兄弟們各依了職業遷居外方,故居初則賃與別家,繼則因兄弟間種種關係,不得不把先人又過辛苦歷史的高大屋宇,受讓給附近的爆發戶,於是兄弟們回故鄉的機會就少,而妹也已有六七年無歸寧的處所了。這次相見,彼此既快樂又酸辛,小孩之中,竟有未曾見過姑母的。外甥女當然不認得舅妗和表姊,雖經大人指導勉強稱呼,總都是呆呆的相覷着。
新居在一個學校附近,背山臨水,地位清靜,只不過平屋四間。論其構造,連老屋的廚房還比不上,妹卻極口表示滿意:
“雖比不上老屋,終究是自己的房子,我家在本地已有多年沒有房子了!自從老屋賣去以後,我有多少被人瞧不起!每次乘船經過老屋面前真是……”
妻見妹說時眼圈有點紅了,就忙用話岔開:
“妹妹你看,我老了許多罷?你卻總是這樣後生。”
“三姊倒不老!——人總是要老的,大家小孩都己這樣大了,他們大起來,就是我們在老起來。我們己六七年不見了呢。”
“快弄飯去罷!”我聽了他們的對話,恐再牽入悲境,故意打斷話頭,使妻走開。
妹自幼從我學會了酒,能略飲幾杯。兄妹且飲且談,嫂也在旁羼着。話題由此及彼,一直談到飯後,還連續不斷。每到妹和妻要談到家事或婆媳小姑關係上去,我總立即設法打斷,因爲我是深知道妹在夫家的境遇的,很不願再難得晤面的當初,就引起悲懷。
忽然,天花板上起了嘈雜的鼠聲。
“新造的房子,老鼠就這樣多嗎?”妹驚訝了問。
“大概是近山的緣故罷。據說房子未造好就有了老鼠的。晚上更厲害,今夜你聽,好像在打仗哩,你們那裏怎樣?”妻說。
“還好,我家有貓。——快要產小貓了,將來可捉一隻來。”
“貓也大有好壞,壞的貓老鼠不捕,反要偷食,到處撒屎,倒是不養好。”我正在尋覓輕鬆的話題,就順了勢講道貓上去。
“貓也和人一樣,有種子好不好的,我那裏的貓,是好種,不偷食,每朝把屎撒在盛灰的畚斗裏。——你記得從前老四房裏有一支好貓罷。我們那隻貓,就是從老四房討去的小貓。近來聽說老四房裏斷了種了,——每年生一胎,附近養蠶的人家都來千求萬懇的討,據說討去都不淘氣的。現在又快要生小貓了。”
老四房裏的那隻貓向來有名。最初的老貓,是曾祖在世時,就有了的,不知是哪裏得來的種子,白地,小黃黑花斑,毛色很嫩,望上去像上等的狐皮“金銀嵌”。善捉鼠性質卻柔順的了不得,當我小的時候,常去抱來玩弄,聽它念肚裏佛,挖看它的眼睛,不啻是一個小伴侶。後來我由外面回家,每走到老四房去,有時還看見這小伴侶——的子孫。曾也想討一隻小貓到家裏去養,終難得逢到恰好有小貓的機會,自遷居他鄉,十年來久不憶及了,不料現在種子未絕,妹家現在所養的,不知已是最初老貓的幾世孫了。家道中落以來,田產室廬大半蕩盡,而曾祖時代的貓,尚間接地在妹家留着種子,這真是一種不可思議的緣,值得叫人無限感興的了。
“哦!就是那隻貓的種子!好的,將來就給我們一隻。那隻貓的種子是近地有名的。花紋還沒有變嗎?”
“你喜歡哪一種?——大約一胎多則三隻,少則兩隻,其中大概有一隻是金銀嵌的,有一二隻是白中帶黑斑的,每年都是如此。”
“那自然要金銀嵌的囉。”我腦中不禁浮出孩時小伴侶的印象來。更聯想到那如雲的往事,爲之茫然。
妻和妹之間,貓的談話,仍被繼續着,兒女中大些的張了眼聽,最小的阿滿,搖着妻的膝問“小貓幾時會來?”我也靠在藤椅上吸着煙默然聽她們。
“小貓的時候,要教會它纔好。如果撒屎在地板上了,就捉到撒屎的地方,當着它的屎打,到碗中偷食吃的時候,就把碗擺在它的前面打,這樣打了幾次,它就不敢亂撒屎多偷食了。”
妹的貓教育論,引得大家都笑了。
次晨,妹說即須回去,約定過幾天再來久留幾日,臨走的時候還說:
“昨晚上老鼠吵得真厲害,下次來時,替你們把貓捉來罷。”
妹去後,全家多了一個貓的話題。最性急的自然是小孩,他們常問“姑媽幾時來?”其實都是爲貓而問,我雖每回答他們“自然會來的,性急什麼?”而心裏也對於那與我家一系有二十多年曆史的貓,懷着迫切的期待,巴不得妹——貓快來。
妹的第二次來,在一個月以後,帶來的只是贈送小孩的果物和若干種的花草和苗種,並沒有貓。說前幾天纔出生,要一個月後方可離母,此次生了三隻,一隻是金銀嵌的,其餘兩隻,是黑白花和狸斑花的,討的人家很多,已替我們把金銀嵌的留定了。
貓的被送來,已是妹第二次回去後半月光景的事,那時已過端午,我從學校回去,一進門妻就和我說:
“妹妹今天差人把貓送來了,她有一封信在這裏。說從回去以後就有些不適應。大約是寒熱,不要緊的。”
我從妻手裏接了信草草一看,同時就向室中四望:
“貓呢?”
“她們在弄它,阿吉阿滿,你們把貓抱來給爸爸看看!”
立刻,柔弱的“尼亞尼亞”聲從房中聽得阿滿抱出貓來:
“會念佛的,一到就蹲在牀下,媽說它是新娘子呢。”
我在女兒手中把小貓熟視着說:
“還小呢,別去捉它,放在地上,過幾天會熟的。當心碰見狗!”
阿滿將貓放下。貓把背一聳就踉蹌得向房裏遁去。接着就從房內發出柔弱的“尼亞尼亞”的叫聲。
“去看看它躲在什麼地方。”阿吉和阿滿躡着腳進房去。
“不要去捉它啊!”妻從後叮囑她們。
貓確是金銀嵌,雖然產毛未退,黃白還未十分奪目,盡足依約地喚起從前老四房裏的小伴侶的印象。“尼亞尼亞”的叫聲,和“咪咪”的呼叫聲,在一家中起了新氣氛,在我心中卻成了一個聯想過去的媒介,想到兒時的趣味,想到家況未中落時的光景。
與貓同來的,總以爲不成問題的妹的病消息,一二日後竟由沉重而至於危篤,終於因惡性瘧疾引起了流產,一下未足月的女孩兒棄去這世界了。
一家人蔘與喪事完畢從喪家回來,一進門就聽到“尼亞尼亞”的貓聲。
“這貓真不利,它是首先來報妹妹的死信的!”妻見了貓嘆息着說。
貓正在在檐前伸了小足爬搔着柱子,突然見我們來,就踉蹌逃去,阿滿趕到櫥下把它捉來了,捧在手裏:
“你不要逃,都是你不好!媽!快打!”
“畜牲曉得什麼?唉,真不利!”妻呆呆的望着貓這樣說,忘記了自己的矛盾,倒弄得阿滿把貓捧在手裏瞪目茫然了。
“把它關在伙食間裏,別放它出來!”我一壁說一壁懶懶地走入臥室睡去。我實在已怕看這貓了。
立時從伙食間裏發出“尼亞尼亞”的悲鳴聲和嘈雜的搔爬聲來。努力想睡,總是睡不着。原想起來把貓重新放出,終於無心動彈,連向那就在房外的妻女叫一聲“把貓放出”的心緒也沒有,只讓自己聽着那連續的貓聲,一味沉浸在悲哀裏。
從此以後,這小小的貓在全家成了一個聯想死者的媒介,特別的在我,這貓所暗示的新的悲哀的創傷,是用了家道中落等類的悵惘包裹着的。
傷逝的悲懷,隨着暑期一天一天地淡去,貓也一天一天地長大,從前被全家所詛咒的這不幸的貓,這時漸被全家寵愛珍惜起來了,當作了死者的紀念物。每餐給它吃魚,歸阿滿飼它,晚上抱進房裏,防恐被人偷了或是被野狗咬傷。
白玉也似的毛地上,黃黑斑錯落的非常明顯,當那蹲在草地上或跳擲在鳳仙花從裏的時候,望去真是美麗。每當附近四鄰或路過的人,見了稱讚說:“好貓!”的時候,妻臉上就現出一種莫可言說的矜誇,好像是養着一個好兒子或是好女兒。特別地是阿滿:
“這是我家的貓,是姑母送來的,姑母死了,就剩了這隻貓了!”她當有人來稱讚這貓的時候,不管那些人陌生與不陌生,總會睜圓了眼起勁地對他說明這些。
貓做了一家的寵兒了,每餐食桌旁總有它的位置,偶然偷了食或是亂撒了屎,雖然依妹的教育法是要就地罰打的,妻也總看妹面上寬恕過去。阿吉阿滿一從學校裏回來就用了帶子逗它玩,或是捉迷藏似地在庭間追趕它。我也常於初秋的夕陽中坐在檐下對了這跳擲小動物作種種的遐想。
那時快近中秋的一個晚上的事:湖上鄰居的幾位朋友,晚飯後散步到了我家裏,大家在月下閒話,阿滿和貓在草地上追逐着玩。客去後,我和妻搬進几椅正要關門就寢,妻照例記起貓來:
“咪咪!”
“咪咪!”阿吉阿滿也跟着喚。
可是卻聽不到貓的“尼亞尼亞”的回答。
“沒有呢!哪裏去了?阿滿,不是你捉出來的嗎?去尋來!”妻着急起來了。
“剛剛在天井裏的[]。”阿滿瞠了眼含糊地回答,一壁哭了起來。
“還哭!都是你不好!夜了還捉出來做什麼呢?——咪咪咪咪!”妻一壁責罵阿滿一壁嗄了聲再喚。
可是仍聽不到貓的“尼亞尼亞”的回答。
叫小孩睡好了,重新找尋,室內室外,東鄰西舍,到處分頭都尋遍,哪有貓的影兒?連方纔談天的幾位朋友都過來幫着在月光下尋覓,也終於不見形影。一直鬧到十二點多鐘月亮已照屋角爲止。
“夜深了,把窗門暫時開着,等它自己回來罷,——偷食沒有日偷的,或者被狗咬死了,但又不聽見它叫。也許不至於此,今夜且讓它去罷。”我寬慰着妻,關了大門,先入臥室去。在枕上還聽到妻的“咪咪”的呼聲。
貓終於不回來。從次日起,一家好像失了什麼似地,都覺到說不出的寂寥。小孩從放學回來也不如平日的高興,特別地在我,於妻女所感的的以外,頓然失卻了沉思過去種種悲歡往事的媒介物,覺得寂寥更甚。
第三日傍晚,我因寂寥不過了,獨自在屋後山邊散步,忽然在山腳田坑中發現貓的屍體。全身黏着水泥,軟軟的倒在坑裏,毛貼着肉,身軀細了好些,項有血跡,似確是被狗或者野獸咬斃了的。
“貓在這裏!”我不自覺叫了說。
“在哪裏?”妻和女孩先後跑來,見了貓都呆呆地幾乎一時說不出話。
“可憐!定是野狗咬死的。阿滿,都是你不好!前晚你不捉它出來,哪裏會死呢?下世去要成冤家啊!——唉!妹妹死了,連妹妹給我們的貓也死了。”妻說時聲音嗚咽了。
阿滿哭了,阿吉也呆着不動。
“進去罷,死了也就算了,人都要死哩,別說貓!快叫人來把它葬了。”我催她們離開。
妻和女孩進去了。我向貓作了最後的一瞥,在昏黃中獨自徘徊。日來已失去了聯想媒介的無數往事,都回光返照似的一時強烈地齊現到心上來了。
二、《雪松上的淚珠》劉白羽
今天上午,到園中散步,清秋睛好,陽光和煦。我從一棵雪松下走過,偶一仰首,看到上面有一點點小珍珠一樣的東西在閃閃發亮,此一發現,引起我心中一瞬間的喜悅。仔細看時,原來是一枝輕細的松枝上掛着一串小小的水珠,於是使我想起昨天夜晚,紅色的閃電突然一亮,響起一陣暴烈的雷聲,窗玻璃上佈滿一片雨珠。雪松本來就是枝葉輕巧,婀娜婆娑,在它上面掛上的雨珠,使我感到那樣精緻,那樣美妙、透明,潔淨發光,每一小點像水晶一樣。忽然間我想起托爾斯泰《戰爭與和平》裏一個人物講的一段話:
“最高的智慧和真理好像最純淨的水,我們希望吸取它。”他說:“我能用不清潔的容器的水,並且指摘它不清潔嗎?只有自身清潔了,我才能使這水保持一定程度的清潔。”
我停下來仔細觀看,我的神經靈敏地想到宇宙是最純潔的,這是從宇宙深處流下的淚水。靈魂是最純潔的,這是從靈魂深處流下的淚水。不,這是我一個失去親人的孤苦的老人心靈中溢出的淚水。
我非常痛楚,我非常悲哀。忽然間一陣小小秋風吹來,這棵高大的雪松整個兒都在簌簌地動,於是千萬顆水珠都在顫動,在搖晃。
於是我想到一次高燒昏熱中偶然醒轉,一剎那間看到輸液的玻璃管裏那生命之水。
於是我想到第一場春雨來時,在我窗玻璃上留下像一隻只微微扇動着的小蜜蜂一樣的帶來春天的生氣的水。
我放輕腳步,從那棵高大挺拔的雪松下走開了。但我又回過頭來,我覺得我臉頰上也有一滴水,一滴滴大自然的淚珠,一滴滴人生的淚珠,它堅貞、純淨、無我無私。讓它給陽光照得更明亮,更明亮吧!這雪松枝上聖靈的純潔的水珠啊!
三、《狗這一輩子》劉亮程
一條狗能活到老,真是件不容易的事。太厲害不行,太懦弱不行,不解人意、太解人意了均不行。總之,稍一馬虎便會被人燉了肉剝了皮。狗本是看家守院的,更多時候卻連自己都看守不住。
活到一把子年紀,狗命便相對安全了,倒不是狗活出了什麼經驗。儘管一條老狗的見識,肯定會讓一個走遍天下的人吃驚。狗卻不會像人,年輕時咬出點名氣,老了便可坐享其成。狗一老,再無人謀它脫毛的皮,更無人敢問津它多病的肉體,這時的狗很像一位歷經滄桑的老人,世界已拿它沒有辦法,只好撒手,交給時間和命。
一條熬出來的狗,熬到拴它的鐵鏈朽了,不掙而斷。養它的主人也入暮年,明知這條狗再走不到哪裏,就隨它去吧。狗搖搖晃晃走出院門,四下裏望望,是不是以前的村莊已看不清楚。狗在早年撿到過一根幹骨頭的沙溝樑轉轉;在早年戀過一條母狗的亂草灘轉轉;遇到早年咬過的人,遠遠避開,一副內疚的樣子。其實人早好了傷疤忘了疼。有頭腦的人大都不跟狗計較,有句俗話:狗咬了你你還能去咬狗嗎?與狗相咬,除了啃一嘴狗毛你又能佔到啥便宜。被狗咬過的人,大都把仇記恨在主人身上,而主人又一古腦把責任全推到狗身上。一條狗隨時都必須準備着承受一切。
在鄉下,家家門口拴一條狗,目的很明確:把門。人的門被狗把持,彷彿狗的家。來人並非找狗,卻先要與狗較量一陣,等到終於見了主人,來時的心境已落了大半,想好的話語也嚇得忘掉大半。狗的影子始終在眼前竄悠,答問間時聞狗吠,令來人驚魂不定。主人則可從容不迫,坐察其來意。這叫未與人來先與狗往。
有經驗的主人聽到狗叫,先不忙着出來,開個門縫往外瞧瞧。若是不想見的人,比如來借錢的,討債的,尋仇的......便裝個沒聽見。狗自然咬得更起勁。來人朝院子裏喊兩聲,自愧不如狗的嗓門大,也就緘默。狠狠踢一腳院門,罵聲"狗日的",走了。
若是非見不可的貴人,主人一趟子跑出來,打開狗,罵一句"瞎了狗眼了",狗自會沒趣地躲開。稍慢一步又會挨棒子。狗捱打捱罵是常有的事,一條狗若因主人錯怪便賭氣不咬人,睜一眼閉一眼,那它的狗命也就不長了。
一條稱職的好狗,不得與其他任何一個外人混熟。在它的狗眼裏,除主人之外的任何面孔都必須是陌生的、危險的。更不得與鄰居家的狗相往來。需要交配時,兩家狗主人自會商量好了,公母牽到一起,主人在一旁監督着。事情完了就完了。萬不可藕斷絲連,弄出感情,那樣狗主人會妒嫉。人養了狗,狗就必須把所有的愛和忠誠奉獻給人,而不應該給另一條狗。
狗這一輩子像夢一樣飄忽,沒人知道狗是帶着什麼使命來到人世。
人一睡着,村莊便成了狗的世界,喧囂一天的人再無話可說,土地和人都乏了。此時狗語大作,狗的聲音在夜空飄來蕩去,將遠遠近近的村莊連在一起。那是人之外的另一種聲音,飄忽、神祕。莽原之上,明月之下,人們熟睡的軀體是聽者,土牆和土牆的影子是聽者,路是聽者。年代久遠的狗吠融入空氣中,已經成寂靜的一部分。
在這衆狗狺狺的夜晚,肯定有一條老狗,默不作聲。它是黑夜的一部分,它在一個村莊轉悠到老,是村莊的一部分,它再無人可咬,因而也是人的一部分。這是條終於可以冥然入睡的狗,在人們久不再去的僻遠路途,廢棄多年的荒宅舊院,這條狗來回地走動,眼中滿是人們多年前的陳事舊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