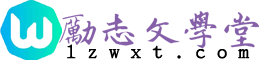豐子愷文章在線閱讀
豐子愷文章在線閱讀

導語:豐子愷是中國現代畫家、散文家、美術教育家、音樂教育家、漫畫家、作家、書法家和翻譯家。這裏本站的小編爲大家整理了三篇豐子愷文章在線閱讀,希望你們喜歡。

一、《黃山印象》
看山,普通總是仰起頭來看的。然而黃山不同,常常要低下頭去看。因爲黃山是羣山,登上一個高峯,就可俯瞰羣山。這教人想起杜甫的詩句“會當凌絕頂,一覽衆山小!”而精神爲之興奮,胸襟爲之開朗。我在黃山盤桓了十多天,登過紫雲峯、立馬峯、天都峯、玉屏峯、光明頂、獅子林、眉毛峯等山,常常爬到絕頂,有如蘇東坡遊赤壁的“履癴巖,披蒙茸,踞虎豹,登虯龍,攀棲鶻之危巢,俯馮夷之幽宮”。
在黃山中,不但要低頭看山,還要面面看山。因爲方向一改變,山的樣子就不同,有時竟完全兩樣。例如從玉屏峯望天都峯,看見旁邊一個峯頂上有一塊石頭很象一隻松鼠,正在向天都峯跳過去的樣子。這景緻就叫“松鼠跳天都”。然而爬到天都峯上望去,這松鼠卻變成了一雙鞋子。又如手掌峯,從某角度望去竟象一個手掌,五根手指很分明。然而峯迴路轉,這手掌就變成了一個拳頭。他如“羅漢拜觀音”、“仙人下棋”、“喜鵲登梅”、“夢筆生花”、“鰲魚駝金龜”等景緻,也都隨時改樣,變幻無定。如果我是個好事者,不難替這些石山新造出幾十個名目來,讓導遊人增加些講解資料。然而我沒有這種雅興,卻聽到別人新取了兩個很好的名目:有一次我們從西海門憑欄俯瞰,但見無數石山拔地而起,真象萬笏朝天;其中有一個石山由許多方形石塊堆積起來,竟同玩具中的積木一樣,使人不相信是天生的,而疑心是人工的。導遊人告訴我:有一個上海來的遊客,替這石山取個名目,叫做“國際飯店”。我一看,果然很象上海南京路上的國際飯店。有人說這名目太俗氣,欠古雅。我卻覺得有一種現實的美感,比古雅更美。又有一次,我們登光明頂,望見東海(這海是指雲海)上有一個高峯,腰間有一個缺口,缺口裏有一塊石頭,很象一隻蹲着的青蛙。氣象臺裏有一個青年工作人員告訴我:他們自己替這景緻取一個名目,叫做“青蛙跳東海”。我一看,果然很象一隻青蛙將要跳到東海里去的樣子。這名目取得很適當。
翻山過嶺了好幾天,最後逶迤下山,到雲谷寺投宿。這雲谷寺位在羣山之間的一個谷中。由此再爬過一個眉毛峯,就可以回到黃山賓館而結束遊程了。我這天傍晚到達了雲谷寺,發生了一種特殊的感覺,覺得心情和過去幾天完全不同。起初想不出其所以然,後來仔細探索,方纔明白原因:原來雲谷寺位在較低的山谷中,開門見山,而這山高得很,用“萬丈”、“插雲”等語來形容似乎還嫌不夠,簡直可用“凌霄”、“逼天”等字眼。因此我看山必須仰起頭來。古語云:“高山仰止”,可見仰起頭來看山是正常的,而低下頭去看山是異常的。我一到雲谷寺就發生一種特殊的感覺,便是因爲在好幾天異常之後突然恢復正常的原故。這時候我覺得異常固然可喜,但是正常更爲可愛。我躺在雲谷寺宿舍門前的藤椅裏,臥看山景,但見一向異常地躺在我腳下的白雲,現在正常地浮在我頭上了,覺得很自然。它們無心出岫,隨意來往;有時冉冉而降,似乎要闖進寺裏來訪問我的樣子。我便想起某古人的詩句:“白雲無事常來往,莫怪山僧不送迎。”好詩句啊!然而叫我做這山僧,一定閉門不納,因爲白雲這東西是很潮溼的。
此外也許還有一個原因:雲谷寺是舊式房子,三開間的樓屋。我們住在樓下左右兩間裏,中央一間作爲客堂;廊下很寬,佈設桌椅,可以隨意起臥,品茗談話,飲酒看山,比過去所住的文殊院、北海賓館、黃山賓館趣味好得多。文殊院是石造二層樓屋,房間象輪船裏的房艙或火車裏的臥車:約一方丈大小的房間,中央開門,左右兩牀相對,中間靠窗設一小桌,每間都是如此。北海賓館建築宏壯,房間較大,但也是集體宿舍式的:中央一條走廊,兩旁兩排房間,間間相似。黃山賓館建築尤爲富麗堂皇,同上海的國際飯店、錦江飯店等差不多。兩賓館都有同上海一樣的衛生設備。這些房屋居住固然舒服,然而太刻板,太洋化;住得長久了,覺得彷彿關在籠子裏。雲谷寺就沒有這種感覺,不象旅館,卻象人家家裏,有親切溫暖之感和自然之趣。因此我一到雲谷寺就發生一種特殊的感覺。雲谷寺倘能添置衛生設備,採用些西式建築的優點:兩賓館的建築倘能採用中國方式,而加西洋設備,使外爲中用,那纔是我所理想的旅舍了。
這又使我回想起杭州的一家西菜館的事,附說在此:此次我遊黃山,道經杭州,曾經到一個西菜館裏去吃一餐午飯。這菜館採用西式的分食辦法,但不用刀叉而用中國的筷子。這辦法好極。原來中國的合食是不好的辦法,各人的唾液都可能由筷子帶進菜碗裏,拌勻了請大家吃。西洋的分食辦法就沒有這弊端,很應該採用。然而西洋的刀叉,中國人實在用不慣,我們還是裏筷子便當。這西菜館能採取中西之長,創造新辦法,非常合理,很可讚佩。當時我看見座上多半是農民,就恍然大悟:農民最不慣用刀叉,這合理的新辦法顯然是農民教他們創造的。
二、《不肯去觀音院》
普陀山,是舟山羣島中的一個島,島上寺院甚多,自古以來是佛教勝地,香火不絕。浙江人有一句老話:“行一善事,比南海普陀去燒香更好。”可知南海普陀去燒香是一大功德。因爲古代沒有汽船,只有帆船;而渡海到普陀島,風浪甚大,旅途艱苦,所以功德很大。現在有了汽船,交通很方便了,但一般信佛的老太太依舊認爲一大功德。
我赴寧波旅行寫生,因見春光明媚,又覺身體健好,遊興濃厚,便不肯回上海,卻轉赴普陀去“借佛遊春”了。我童年時到過普陀,屈指計算,已有五十年不曾重遊了。事隔半個世紀,加之以解放後普陀寺廟都修理得嶄新,所以重遊竟同初遊一樣,印象非常新鮮。
我從寧波乘船到定海,行程三小時;從定海坐汽車到沈家門,五十分鐘;再從沈家門乘輪船到普陀,只費半小時。其時正值二月十九觀世音菩薩生日,香客非常熱鬧,買香燭要排隊,各寺院客房客滿。但我不住寺院,住在定海專署所辦的招待所中,倒很清靜。
我遊了四個主要的寺院:前寺、後寺、佛頂山、紫竹林。前寺是普陀的領導寺院,殿宇最爲高大。後寺略小而設備莊嚴,千年以上的古木甚多。佛頂山有一千多石級,山頂常沒在雲霧中,登樓可以俯瞰普陀全島,遙望東洋大海。紫竹林位在海邊,屋宇較小,內供觀音,住居者盡是尼僧;近旁有潮音洞,每逢潮漲,濤聲異常宏亮。寺後有竹林,竹竿皆紫色。我曾折了一根細枝,藏在衣袋裏,帶回去作紀念品。這四個寺院都有悠久的歷史,都有名貴的古物。我曾經參觀兩隻極大的飯鍋,每鍋可容八九擔米,可供千人吃飯,故名曰“千人鍋”。我用手杖量量,其直徑約有兩手杖。我又參觀了一隻七千斤重的鐘,其聲宏大悠久,全山可以聽見。
這四個主要寺院中,紫竹林比較的最爲低小;然而它的歷史在全山最爲悠久,是普陀最初的一個寺院。而且這開國元勳與日本人有關。有一個故事,是紫竹林的一個尼僧告訴我的,她還有一篇記載掛在客廳裏呢。這故事是這樣:千餘年前,後梁時代,即公曆九百年左右,日本有一位高僧,名叫慧鍔的,乘帆船來華,到五臺山請得了一位觀世音菩薩像,將載回日本去供養。那帆船開到蓮花洋地方,忽然開不動了。這慧鍔法師就向觀音菩薩禱告:“菩薩如果不肯到日本去,隨便菩薩要到哪裏,我和尚就跟到哪裏,終身供養。”禱告畢,帆船果然開動了。隨風飄泊,一直來到了普陀島的潮音洞旁邊。慧鍔法師便捧菩薩像登陸[]。此時普陀全無寺院,只有居民。有一個姓張的居民,知道日本僧人從五臺山請觀音來此,就捐獻幾間房屋,給他供養觀音像。又替這房屋取個名字,叫做“不肯去觀音院”。慧鍔法師就在這不肯去觀音院內終老。這不肯去觀音院是普陀第一所寺院,是紫竹林的前身。紫竹林這名字是後來改的。有一個人爲不肯去觀音院題一首詩:
借問觀世音,因何不肯去?
爲渡大中華,有緣來此地。
如此看來,普陀這千餘年來的佛教名勝之地,是由日本人創始的。可見中日兩國人民自古就互相交往,具有密切的關係。我此次出遊,在寧波天童寺想起了五百年前在此寺作畫的雪舟,在普陀又聽到了創造寺院的慧鍔。一次旅行,遇到了兩件與日本有關的事情,這也可證明中日兩國人民關係之多了。不僅古代而已,現在也是如此。我經過定海,參觀魚場時,聽見漁民說起:近年來海面常有颶風暴發,將漁船吹到日本,日本的漁民就招待這些中國漁民,等到風息之後護送他們回到定海。有時日本的漁船也被颶風吹到中國來,中國的漁民也招待他們,護送他們回國。勞動人民本來是一家人。
不肯去觀音院左旁,海邊上有很長、很廣、很平的沙灘。較小的一處叫做“百步沙”,較大的一處叫做“千步沙”。潮水不來時,我們就在沙上行走。腳踏到沙上,軟綿綿的,比踏在芳草地上更加舒服。走了一陣,回頭望望,看見自己的足跡連成一根長長的線,把平淨如鏡的沙面劃破,似覺很可惜的。沙地上常有各種各樣的貝殼,同遊的人大家尋找拾集,我也拾了一個藏在衣袋裏,帶回去作紀念品。爲了拾貝殼,把一片平沙踩得破破爛爛,很對它不起。然而第二天再來看看,依舊平淨如鏡,一點傷痕也沒有了。我對這些沙灘頗感興趣,不亞於四大寺院。
離開普陀山,我在路途中作了兩首詩,記錄在下面:一別名山五十春,重遊佛頂喜新晴。
東風吹起千巖浪,好似長征奏凱聲。
寺寺燒香拜跪勤,莊嚴寶島氣氤氳。
觀音頷首彌陀笑,喜見羣生樂太平。
回到家裏,摸摸衣袋,發見一個貝殼和一根紫竹,聯想起了普陀的不肯去觀音院,便寫這篇隨筆。
三、《大賬簿》
我幼年時,有一次坐了船到鄉間去掃墓。正靠在船窗口出神觀看船腳邊層出不窮的波浪的時候,手中拿着的不倒翁一剎那間形影俱杳,全部交付與不可知的渺茫的世界了。我看看自己的空手,又看看窗下的層出不窮的波浪,不倒翁失足的傷心地,再向船後面的茫茫白水悵望了一會,心中黯然地起了疑惑與悲哀。我疑惑不倒翁此去的下落與結果究竟如何,又悲哀這永遠不可知的命運。它也許隨了波浪流去,擱住在岸灘上,落入於某村童的手中;也許被魚網打去,從此做了漁船上的不倒翁;又或永遠沉淪在幽暗的河底,歲久化爲泥土,世間從此不再見這個不倒翁。我曉得這不倒翁現在一定有個下落,將來也一定有個結果,然而誰能去調查呢?誰能知道這不可知的命運呢?這種疑惑與悲哀隱約地在我心頭推移。終於我想:父親或者知道這究竟,能解除我這種疑惑與悲哀。不然,將來我年紀長大起來,總有一天能知道這究竟,能解除這疑惑與悲哀。
後來我的年紀果然長大起來。然而這種疑惑與悲哀,非但依舊不能解除,反而隨了年紀的長大而增多增深了。我偕了小學校裏的同學赴郊外散步,偶然折取一根樹枝,當手杖用了一會,後來拋棄在田間的時候,總要對它回顧好幾次,心中自問自答:“我不知幾時得再見它?它此後的結果不知究竟如何?我永遠不得再見它了!它的後事永遠不可知了!”倘是獨自散步,遇到這種事的時候我更要依依不捨地留連一回。有時已經走了幾步,又迴轉身去,把所拋棄的東西重新拾起來,鄭重地道個訣別,然後硬着頭皮拋棄它,再向前走。過後我也曾自笑這癡態,而且明明曉得這些是人生中惜不勝惜的瑣事;然而那種悲哀與疑惑確實地充塞在我的心頭,使我不得不然!
在熱鬧的地方,忙碌的時候,我這種疑惑與悲哀也會被壓抑在心的底層,而安然地支配取捨各種事物,不復作如前的癡態。間或在動作中偶然浮起一點疑惑與悲哀來;然而大衆的感化與現實的壓迫的力非常偉大,立刻把它壓制下去,它只在我的心頭一閃而已。一到靜僻的地方,孤獨的時候,最是夜間,它們又全部浮出在我的心頭了。燈下,我推開算術演草簿,提起筆來在一張廢紙上信手塗寫日間所諳誦的詩句:“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沒有寫完,就拿向燈火上,燒着了紙的一角。我眼看見火勢孜孜地蔓延過來,心中又忙着和個個字道別。完全變成了灰燼之後,我眼前忽然分明現出那張字紙的完全的原形;俯視地上的灰燼,又感到了暗淡的悲哀:假定現在我要再見一見一分鐘以前分明存在的那張字紙,無論託紳董、縣官、省長、大總統,仗世界一切皇帝的勢力,或堯舜、孔子、蘇格拉底、基督等一切古代聖哲復生,大家協力幫我設法,也是絕對不可能的事了!——但這種奢望我決計沒有。我只是看看那堆灰燼,想在沒有區別的微塵中認識各個字的死骸,找出哪一點是春字的灰,哪一點是蠶字的灰。……又想象它明天朝晨被此地的僕人掃除出去,不知結果如何:倘然散入風中,不知它將分飛何處?春字的灰飛入誰家,蠶字的灰飛入誰家?……倘然混入泥土中,不知它將滋養哪幾株植物?……都是渺茫不可知的千古的大疑問了。
吃飯的時候,一顆飯粒從碗中翻落在我的衣襟上。我顧視這顆飯粒,不想則已,一想又惹起一大篇的疑惑與悲哀來:不知哪一天哪一個農夫在哪一處田裏種下一批稻,就中有一株稻穗上結着煮成這顆飯粒的谷。這粒谷又不知經過了誰的刈、誰的磨、誰的舂、誰的糶,而到了我們的家裏,現在煮成飯粒,而落在我的衣襟上。這種疑問都可以有確實的答案;然而除了這顆飯粒自己曉得以外,世間沒有一個人能調查,回答。
袋裏摸出來一把銅板,分明個個有複雜而悠長的歷史。鈔票與銀洋經過人手,有時還被打一個印;但銅板的經歷完全沒有痕跡可尋。它們之中,有的曾爲街頭的乞丐的哀願的目的物,有的曾爲勞動者的血汗的代價,有的曾經換得一碗粥,救濟一個餓夫的飢腸,有的曾經變成一粒糖,塞住一個小孩的啼哭,有的曾經參與在盜賊的贓物中,有的曾經安眠在富翁的大腹邊,有的曾經安閒地隱居在毛廁的底裏,有的曾經忙碌地兼備上述的一切的經歷。且就中又有的恐怕不是初次到我的袋中,也未可知。這些銅板倘會說話,我一定要尊它們爲上客,恭聽它們歷述其漫遊的故事。倘然它們會紀錄,一定每個銅板可着一冊比《魯濱遜飄流記》更奇離的奇書。但它們都象死也不肯招供的犯人,其心中分明祕藏着案件的是非曲直的實情,然而死也不肯泄漏它們的祕密。
現在我已行年三十,做了半世的人。那種疑惑與悲哀在我胸中,分量日漸增多;但刺激日漸淡薄,遠不及少年時代以前的新鮮而濃烈了。這是我用功的結果。因爲我參考大衆的態度,看他們似乎全然不想起這類的事,飯吃在肚裏,錢進入袋裏,就天下太平,夢也不做一個。這在生活上的確大有實益,我就拼命以大衆爲師,學習他們的幸福。學到現在三十歲,還沒有畢業。所學得的,只是那種疑惑與悲哀的刺激淡薄了一點,然其分量仍是跟了我的經歷而日漸增多。我每逢辭去一個旅館,無論其房間何等壞,臭蟲何等多,臨去的時候總要低徊一下子,想起“我有否再住這房間的一日?”又慨嘆“這是永遠的訣別了!”每逢下火車,無論這旅行何等勞苦,鄰座的人何等可厭,臨走的時候總要發生一種特殊的感想:“我有否再和這人同座的一日?恐怕是對他永訣了!”但這等感想的出現非常短促而又模糊,象飛鳥的黑影在池上掠過一般,真不過數秒間在我心頭一閃,過後就全無其事。我究竟已有了學習的工夫了。然而這也全靠在老師——大衆——面前,方始可能。一旦不見了老師,而離羣索居的時候,我的故態依然復萌。現在正是其時:春風從窗中送進一片白桃花的花瓣來,落在我的原稿紙上。這分明是從我家的院子裏的白桃花樹上吹下來的,然而有誰知道它本來生在哪一枝頭的哪一朵花上呢?窗前地上白雪一般的無數的花瓣,分明各有其故枝與故萼,誰能一一調查其出處,使它們重歸其故萼呢?疑惑與悲哀又來襲擊我的心了。
總之,我從幼時直到現在,那種疑惑與悲哀不絕地襲擊我的心,始終不能解除。我的年紀越大,知識越富,它的襲擊的力也越大。大衆的榜樣的壓迫愈嚴,它的反動也越強。倘一一記述我三十年來所經驗的此種疑惑與悲哀的事例,其卷帙一定可同《四庫全書》、《大藏經》爭多。然而也只限於我一個人在三十年的短時間中的經驗;較之宇宙之大,世界之廣,物類之繁,事變之多,我所經驗的真不啻恆河中的一粒細沙。
我彷彿看見一冊極大的大帳簿,簿中詳細記載着宇宙間世界上一切物類事變的過去、現在、未來三世的因因果果。自原子之細以至天體之巨,自微生蟲的行動以至混沌的大劫,無不詳細記載其來由、經過與結果,沒有萬一的遺漏。於是我從來的疑惑與悲哀,都可解除了。不倒翁的下落,手杖的結果,灰燼的去處,一一都有記錄;飯粒與銅板的來歷,一一都可查究;旅館與火車對我的因緣,早已註定在項下;片片白桃花瓣的故萼,都確鑿可考。連我所屢次嘆爲永不可知的、院子裏的沙堆的沙粒的數目,也確實地記載着,下面又註明哪幾粒沙是我昨天曾經用手掬起來看過的。倘要從沙堆中選出我昨天曾經掬起來看過的沙,也不難按這帳簿而探索。——凡我在三十年中所見、所聞、所爲的一切事物,都有極詳細的記載與考證;其所佔的地位只有書頁的一角,全書的無窮大分之一。
我確信宇宙間一定有這冊大帳簿。於是我的疑惑與悲哀全部解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