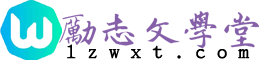王充閭:靈魂的拷問
王充閭:靈魂的拷問

題記
我喜歡踏尋古蹟。定居瀋陽二十多年,凡是在歷史上有點名堂的地方,幾乎我都到過;唯獨龍王廟的遺址至今還不知其確切所在。翻遍了各種書,也問過許多人,最後還是茫然不曉。這也難怪,因爲它原本是清代初年佈滿盛京的幾百座廟宇中最普通的一座,而且,可能坐落在城外的渾河岸邊,料想也是非常簡陋的。只是由於一位名人在裏面寄宿過很長一段時間,才使它與衆有所不同,在史書上留下了名字。
我說的這個人名叫陳夢雷。他是有清一代赫赫有名的大學者,康熙年間的翰林院編修,編纂過着名的典籍《古今圖書集成》。在一次突發事件中,陳夢雷被他的“知心朋友”李光地出賣了,結果,人家吞功邀寵,步步蓮花,享不盡的榮華富貴;而他卻險些腦袋搬了家,後來虧得同僚說情,聖上開恩,被判作戴罪流放,流落到此間給一戶披甲的滿族之家當奴隸,幹苦力。
提起這類背信棄義,賣友求榮的勾當,心裏總是覺得十分沉重,鬱悶雜着苦澀,很不是滋味。看來,它同嫉妒、貪婪、欺詐、陰險一樣,都屬於人性中惡的一面,即便算不上常見病、多發病,恐怕也將伴隨着人類的存在而世代傳承,綿延不絕。“啊,朋友!這世界上本來就沒有朋友。”亞里士多德的這番話,未免失之過激,但它肯定植根於切身的生命感受,實爲傷心悟道之言。
遠的不去說它,只就我們這輩人的有限經歷來講,大概很多人對於過去一些政治運動中的投機、誣陷、傾軋,直至出賣朋友的行徑,都不會感到生疏。而當這種種惡行發生於那種“政治異化”過程中,則更是花樣翻新,變本加厲。有些人竟然以革命的名義,在“打倒走資派”、“批鬥資產階級學術權威”、“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堂堂正正的旗幟下,有組織有領導地大張旗鼓地公開進行。在這種情勢下,那些充滿個人的無助感、卑微感、絕望感的受害者,迫於當時的強大攻勢,不大可能進行絕交、申討之類的直接對抗。加之在所謂“羣體性的歷史災難”中,個人的卑劣人性往往被“時代悲劇”、“體制缺陷”等重重迷霧遮掩起來,致使大多數人更多地着眼於社會環境因素,而輕忽了、淡化了個人應負的道義責任。充其量,止於就事論事,辨明是非,而很少有人能夠燭隱抉微,透過具體事件去進行心靈的探察,靈魂的拷問。
世事駁雜,人生多故,我們究竟應當如何面對這類問題?輕輕地放過,固然不可取,但簡單的牙眼相還,睚眥必報,也只是一時痛快而已。我以爲,不妨參照陳夢雷的做法,堅定地守護着思想者的權利,在痛定思痛,全面披露事實真相的同時,能夠深入到心靈的底層,從人性的層面上,揭示那班深文周納、陷人於罪者居心之陰險,手段之齷齪,靈魂的醜惡。這樣,不僅有功於世道人心,爲後來者提供一些寶貴的人生教訓;而且,可以淨化靈魂,警戒來者,防止類似的人間悲劇重演。
從這個意義上說,今天我們拂去歲月的埃塵,翻開三百多年前的史頁,舊案重溫,再現陳夢雷上當受騙,沉冤難雪,終於痛寫《絕交書》,使真相大白於天下的血淚交進的歷程,確是不無教益的。
難友
陳夢雷出身於一個富有文化教養的詩書門第,父親教子有方,管束極嚴,在他的身上傾注了全部心血。因而,他得以年少登科,剛剛十二歲就入泮成了秀才;八年後參加鄉試中了舉人;又過了一年便高中庚戌科的二甲進士,被選爲翰林院庶吉士,不久即授翰林院編修。真是春風得意,平步青雲。康熙十二年,由於母親在京師不服水土,他臨時請假護送南歸,返回原籍福建侯官(福州),從而結束了三載安富尊榮的京宦生涯。這一年剛剛二十五歲。他萬萬沒有想到,此番南下竟成了他“運交華蓋”的人生轉折點。可憐一枕還鄉夢,斷送功名到白頭!
陳夢雷回到家鄉不久,就趕上了“三藩之亂”爆發,靖南王耿精忠擁兵自重,據閩叛清,一時間鬧得人心浮蕩,滿城風雨。爲了網羅名士,壯大聲威,硬逼着陳夢雷改換門庭,出任僞翰林院編修,由於本人拒不接受,而降授爲戶部員外。陳夢雷無奈,便披緇削髮,躲進了僧寺,託病不出。叛軍還是不依不饒,三天兩頭地催逼就道,他脫身無計,只好虛與委蛇,準備尋覓機會一走了之。
就在這時,與他同爲福建鄉親,同年考中二甲進士,同爲翰林院編修,而且有很深交情的李光地,也因爲探親返回了家鄉。由於李光地是着名的理學家,在當地名氣很大,耿精忠想要藉助他的聲望招搖作勢,便派人到他的安溪故里,召他出仕。他趁着耿精忠親自接見的機會,悄悄來到了侯官,暗地裏與陳夢雷會面。兩個知心朋友好久沒在一起談心了,而今難裏重逢,自有訴不盡的衷腸,說不完的款曲,足足傾談了三個晚上,內容主要是圍繞着如何對待面臨的艱危形勢,籌謀應付叛軍的對策。
他們考慮到,陳夢雷已經陷身羅網,輕易脫不了身,只好因勢乘便,暫時留下來出面周旋,同時做一些瞭解內情、瓦解士心的工作,待討耿清軍一到,便做好內應,以應時變;而尚未出任僞職的李光地,則趕緊藏匿起來,並且儘快逃離福建,然後設法與朝廷取得聯繫,密報耿軍實情,剖白兩個落難臣子的耿耿忠心。
握別時,陳夢雷激動不已,當即向李光地誓約:他日如能幸見天日,那時我們當互以節操鑑證;倘若時命相左,未能得償夙願,後死者也當會通過文字來展示實情,使天下後世知道,大清國養士三十餘年,在海濱萬里之遙的八閩大地,還有一兩個矢志守節的孤臣,死且不朽。李光地聽了這番情辭懇切的內心剖白,頗有一番感慨,在點頭稱許之餘,趁便向陳夢雷提出代爲照料家中百口的要求,並囑咐他安心在這裏留守:“光復之日,汝之事全部包在我的身上。”
這樣,李光地便放下心來,返回安溪,然後遁跡深山,籌措出逃之計。由於此間遠離侯官六百餘里,消息十分閉塞,爲了更多地掌握耿軍內情,瞭解其發展態勢,他又幾次派人專門到陳夢雷那裏去打探虛實,進一步摸清底細,以便北上之後,向朝廷進獻討逆破敵之策。
過了不多日子,李光地就順利出逃了。在陳夢雷的多方周旋下,叛軍對李潛逃一事沒有加以深究,其家口也賴以保證了安全。這壁廂的陳夢雷,身處叛軍之中,如坐鍼氈,度日如年,日夜翹首北望,企盼着摯友有信息傳來;那壁廂的李光地,脫開虎口之後,則鴻飛冥冥,杳無蹤影,再也沒有隻言片紙告慰別情。原來,他已經把由陳夢雷提供的耿軍內情和行陣虛實全部整理成文字,用蠟丸封好,作爲密疏上報給朝廷,並提出建議:南下清軍應以急攻爲主,不宜遷延歲月,以免日久生變。而密疏上卻只署了自己的名字,絲毫沒有提及陳夢雷曾經參與其事。康熙皇帝得報,如獲至寶,真是“欲渡河而船來”,立刻將它遍示羣臣,同時命令兵部抄寄前方,使將帥知之,採取相應的對策。康熙帝滿口稱讚李光地:“真忠臣也!”很快就加以厚賞重用,超授李光地爲侍講學士。
康熙十六年,清軍收復福建,叛將耿精忠率衆投降。這時,李光地又以平叛功臣和接收大員的姿態再次蒞臨福建,聲威赫赫地出現在侯官衙署。在接見陳夢雷的時候,親口告訴他:“你做了大量盡忠報國的事情,不是一樣兩樣,吾當一一地向皇帝稟告。”並且題詩相贈,有“李陵不負漢,樑公亦反周”之句,讚揚他身在僞朝,不忘邦國,像投降匈奴的李陵、身仕北周的樑士彥那樣,能夠苦心孤詣,勤勞王室。一番經過刻意構思、措辭美妙的甘言旨語,說得滿腦袋書呆子氣的陳夢雷,像是泡在蜜糖罐裏,身心舒坦地回到了家裏,靜候着回黃轉綠、苦盡甘來的佳音。每天每日,他都可憐巴巴地嚮往着:朝廷如何重新啓用他,給他以超格的獎掖;縱不能如此,退出一萬步去,聖上也必能體察孤臣孽子在極端困苦處境中的忠貞不渝的苦心。
萁豆相煎
有道是:無巧不成書。也是合該着陳夢雷倒黴晦氣,“福建之亂”中偏偏有一個叫做陳防的人主動投靠了耿精忠的叛軍,並被授爲翰林院大學士,由於他們同姓,又同在叛軍中供職,結果,京師中就把這個人誤傳爲陳夢雷。爲此,他受到了刑部的傳訊。緊接着,收降的叛軍裏又有人舉報陳夢雷曾經參與倡亂。這樣,刑部便以“從逆”的罪名逮他入獄。陳夢雷萬萬沒有料到會有這一遭兒——靖逆的功臣沒有當上,反倒成了禍患不測的階下囚,正是“有懷莫剖,負謗難明”。
當然,儘管他的深心裏非常痛苦,但還抱有足夠的希望:一是他認爲康熙皇帝洞悉其中內情,最後總會公正、客觀地對待他(他滿以爲李光地已經如實上報了);二是身爲朝廷命官、皇帝寵臣,又對事實真相一清二楚的李光地,更會不忘前情,踐履舊約,鼎力加以營救。可是,他哪裏知道,事實恰好相反,那個滿口應承必定予以厚報的李大老爺,早把這個昔日的“知心朋友”、患難中的救命恩人丟在了九霄雲外。對於面臨滅頂之災的陳夢雷,不但避之唯恐不遠,未置片言隻語以相救援,反而在其着述中,藉着敘述當年在福建的那段遭遇,把陳夢雷寫成甘心事敵還不算,並且企圖陷害朋友于不義,要把他也拉下水,用以表白自己的立場堅定,旗幟鮮明。這麼一“撇清兒”不打緊,可就把陳夢雷送上了絕路——進一步坐實了他的“從逆”罪證,使之成爲一樁鐵案,結果是以死刑論斬。而最後拍板敲定這個死刑案的,恰恰是康熙皇帝。
對於完全出於無奈,被迫就任僞職的陳夢雷——且不說在被拘中他還有立功表現——科以如此重刑,許多與此事毫無瓜葛的局外人,都覺得量刑過於酷峻,未免有失公允;尤其爲李光地的背信棄義、賣友求榮深致憤慨,因而明裏暗裏站在陳夢雷一邊,幫助他說了一些好話。與李光地同爲侍講學士的徐乾學,出於憐才惜士之殷,勸說李光地應恪盡朋友情誼,勇於出面,上疏營救,不要坐視不顧。而李光地卻以“恐怕無濟於事”爲辭加以推脫。在徐乾學一再催促之下,才勉強答應以他的名義上疏,但呈文要由徐乾學來代擬。與此同時,明珠太傅也上殿說情,奏請康熙皇帝從寬發落。最後總算免除了一死,把陳夢雷流放到盛京,給披甲的滿洲主子爲奴。李光地則在紫禁城裏獨享富貴,穩做高官,聲望日隆;視陳夢雷如同陌路之人,未曾有過片紙通問,什麼往日的深恩,當面的承諾,早已淡忘如遺。
對於陳夢雷來說,這場奇災慘禍如果也還有什麼裨益的話,那就是從中認識到仕途的險惡、人事的乖張,也擦亮了眼睛,看清了所謂“知心朋友”的真面目。他是一個心實性善的厚道人,雖說通今博古,滿腹經綸,卻未免過分迂闊,帶有濃重的書生氣。他真正識破李光地的心術與心跡,是經歷了一個曲折而長期的過程的。當他開始得知李光地並沒有在蠟丸中如實披露事實真相時,雖然有些震驚,深感失望,但還覺得情有可原,李光地有其難言之隱,主要是爲了迴護自己,洗清干係,以免橫生枝節;當時他絕沒有料到,李光地竟會趁機傾陷,落井下石,必欲置之於死地而後已。後來,隨着事態的發展,一樁樁一件件令人心膽俱寒的事實亮了出來,才完全暴露出李某人的嘴臉,這使他痛苦到了極點,也痛恨到了極點,正所謂“不救之失小,而下石之恨深”。
他長時期沉浸在極度苦悶之中,有時甚至不想再活下去。平素他是最尊崇孔聖人的,懂得“仁者不憂,智者不惑,勇者不懼”的道理;他也十分欣賞莊子,對於《南華經》中所倡導的心齋、坐忘的超人境界,“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的人生理念,從小就諳熟於心,而且經常說給別人聽,講得頭頭是道;可是,真正臨到了自己頭上,卻無論如何也修煉不到那種火候。他曾經幻想過,哪一天喝上一杯“孟婆茶”,或者飽飲一頓“忘川水”,把過往的一切憤懣、憂煩、傷心、氣惱,統統地丟到耳旁脖子後去;也曾想,學學那位華山道士陳摶老祖,連續睡上一百天,架構一場“夢裏乾坤”,換來一個全新的自我;可是,一切都是徒勞,不要說沉沉地睡上一百天,就連一個晚上也未曾安眠過。那噩夢般的前塵往事,無日無夜不在糾纏着他,困擾着他,直弄得他“千辛百折,寢食不寧”。
經年的困頓已經習慣了,沉重的苦役也可以承擔,包括他人的冷眼、漠視統統都不在話下,唯獨“知心朋友”的恩將仇報,背信棄義,是萬萬難以忍受的。如果說,友誼是痛苦的舒緩劑,哀傷的消解散,沉重壓力的疏泄口,災難到來時的庇護所;那麼,對友誼的背叛與出賣,則無異於災難、重壓、痛苦的集束彈、充氣閥和加油泵,已經膨脹到極點了,憋悶使他片刻也難以忍受;如果不馬上噴發出來,他覺得胸膛就會窒息,或者炸開。因而,在戴罪流放的次年秋天,他滿懷着強烈的憤慨,抱病揮毫,寫下了一紙飽含着血淚的《絕交書》。
拷問(之一)
《絕交書》全文四千餘言,大體上包括四層內容:開頭以少量文字交代寫作意圖;接着敘述他和李光地面對叛軍逼迫,籌謀對策的原委;三、四部分揭露李光地背信吞功、賣友求榮的事實真相,並對此予以痛切的譴責,進行靈魂的拷問,爲全文的重心所在。下面,摘要引述《絕交書》中的部分內容:
自不孝(陳夢雷自稱)定案之後,遊歷寒暑,年兄(指李光地)遂無一介,復通音問,其視不孝不啻握粟呼雞,檻羊哺虎,既入坑阱,不獨心意不屬,抑且舞蹈漸形。蓋從前牢籠排擠之大力深心,至是而高枕矣。
然奏請者有人,援引釋放之例者有人。年兄此時身近綸扉,縮頸屏息,噤不出一語,遂使聖主高厚之恩,僅就免死減等之例,使不孝身淪廝養,跡遠邊庭。
老母見背,不能奔喪;老父倚閭,不能歸養。而此時年兄晏然擁從嗚騶,高談闊步,未知對子弟何以爲辭?見僕妾何以爲容?坐立起臥,俯仰自念,果何以爲心耶?
夫忘德不酬,視危不救,鄙士類然,無足深責;乃若悔從前之妄,護已往之尤,忌共事之分功,肆下石以滅口,君子可逝不可陷,其誰能堪此也?
……
向使與年兄非同年、同裏、同官,議論不相投,性情不相信,未必決裂至此!
回思十載襟期,恍如下夢,人生不幸,寧有是哉?
引文的大致意思是:
自從我罪案判定之後,已經過去一年多的時間,你老兄連一封書信也沒有寄過,再也不復過問,看來我在你的心目中是沒有絲毫地位的,簡直如同手裏抓着一把米就可以隨意吆喝的小雞,如同圈裏的隨時準備飼虎的綿羊。既然我已經落入陷阱一般,系身牢獄,你不但完全不把我放在心上,而且,高興得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如果說,從前你還有所顧忌的話,那麼,到了現在,過去對我進行牢籠、排擠的大力深心,就完全放了下來,高枕無憂了。
案發之後,許多人都對我表示同情,給予關照,有的給皇帝上疏,奏請聖上法外施恩;有的援引已往的成例,要求將我無罪開釋。那麼,此時正飛黃騰達、身近內閣(明清時宰輔所在之處爲“綸扉”)的你老兄又是怎麼做的呢?你在一旁縮着脖子,屏住氣息,噤若寒蟬,不發一語。致使聖上雖然施恩高厚,也僅僅依照罪行減等之例,免除了我的一死,結果造成我淪爲卑賤的奴隸,流放到遼遠的邊庭。老母去世,我不能前往奔喪;年邁的父親整天地倚門佇望,我也未能歸養。而你老兄,此時卻晏然處之,心安理得,出行時,騎卒傳呼喝道,前呼後擁,坐下來,高談闊論,意氣揚揚。我不知道,對於瞭解情況的子弟們,你將用什麼言辭來交代?見到僕從和妻妾們,怎麼去雕琢粉飾?行走坐臥,輾轉思量,如何才能安頓下這顆心來?
那種知恩不報,見危不救的行爲,如果發生在鄙陋不堪的俗人身上,固然不足加以深深的責備,而你身爲堂堂的理學名臣、一代道德冠冕,竟然這樣掩飾自己從前的過失,不僅獨吞兩人合作共事所獲得的成果,而且心懷嫉恨,暗中落井下石,企圖滅口銷贓。士可殺不可辱,可以從容面對死亡,卻絕不能忍受這種無端的傾陷。
……
我也曾想過,如果我們不是同年登第、同鄉,又同在翰林院供職,如果相互間素無情誼,沒有共同語言,性情也不投合,彼此不相信任,今天大概也不至於決裂到這種程度。你的所作所爲實在太令人痛心疾首了!回想我們十載交情,相互期許,於今恍如一場夢境,全部化作虛無。人生難道還有比這更不幸的嗎?
作者是清代的學問大家、文章巨匠,《絕交書》寫得聲淚交進,震撼心扉;即事論理,層層剖斷,極富說服力、感染力;而且,在敘述策略上也十分考究:他考慮到此文必將流佈天下,並能上達宸聽,因此,充分利用“哀兵必勝”的心理,採取“綿裏藏針”的手法,以爭得廣泛的同情,佔據主動地位。當然,也和中國古代知識分子素來講究“交絕不出惡聲”的傳統禮儀有關。就是說,不到萬不得已,不肯撕破臉皮,把朋友間的齟齬徹底張揚出去;即使公開決裂了,也還要講究說話的方式方法。
晉代的嵇康寫過一篇《與山巨源絕交書》,這在文學史上是赫赫有名的。山濤,字巨源,原本“竹林七賢”之一,後來喪失操守,投靠司馬昭當了選曹郎,他在調升散騎常侍以後,想舉薦嵇康來充任這一職務。當時,司馬氏篡魏自立之勢已成,嵇康在政治上與之處於對立地位。山濤卻要舉以自代,拉着他一同下水,在嵇康看來,這是對他的人格的蔑視與污辱。於是,投書加以拒絕,並斷然與之絕交。
而陳夢雷的這份《絕交書》,則着眼於剖白蠟丸密疏真相,徹底揭露李光地“面諾背違,下石飛矢”的僞君子面孔。這對於滿口仁義道德、孝悌忠恕,以“理學名臣”彰聞於世的李光地來說,無疑是致命的一擊。
因此,一當《絕交書》面世,李光地便立刻授意子弟,組織人四處查收、銷燬。然而,效果不佳,反倒欲蓋彌彰,流傳更爲廣遠,直至“分贈諸師友,轉相抄誦,而使萬人歎賞”了。以不畏權勢名重當時的黃叔威,有一篇評論頗具代表性。他說:《絕交書》“前面多少含忍,後面則痛心已極,無復可奈。不知是淚是血,是筆是墨?其文氣一往奔注,有怒浪翻空,疾雷破柱之勢。”讚揚陳夢雷“慷慨激烈之氣,可以貫金石動鬼神”;“後死有人,當不令如此大節,遺落天壤也”。反過來,對於李光地則痛加鞭撻,竟至呼出:“噫!安得立請上方斬馬劍,一取此輩頭乎!”
拷問(之二)
看到這裏,我想,讀者一定會循着《絕交書》中質問的“何以爲辭”、“何以爲容”、“何以爲心”的線索,提出一系列的問題,比如,李光地如此喪心昧良,難道他就沒有絲毫顧忌嗎?
“首先,他將如何面對陳夢雷這個過去的‘知心朋友’?”
其實,對付的辦法說來也很簡單。當陳夢雷對面責問時,他只是“唯唯而已”。這樣一來,你也就拿他沒有辦法。在“當紅大佬”李光地的心目中,陳夢雷,一個永無翻身之望的戴罪流人,不知哪一天就將填屍溝壑,即使勉強得以苟延殘喘,也是“有若無,實若虛”也,“不啻握粟呼雞,檻羊哺虎”,是可以隨意擺佈,甚至完全否定他的存在,連正眼都無須一瞬的。
“那麼,作爲着名的理學家,孔聖人的後學嫡傳,二程、朱熹的忠實信徒,他總該記得孔夫子的箴言:‘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不能什麼也不怕吧?他總該記得曾子的訓導:‘吾日三省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他在清夜無眠之時,總該捫心自問:爲人處世是否於理有虧,能否對得起天地良心吧?難道他就不怕良心責備嗎?”
“三畏”、“三省”的修養功夫,孔、孟、顏、曾提出的當日,也許是準備認真施行的;而當到了後世的理學家手裏,便成了傳道的教條,專門用以勸誡他人,自己卻無須踐行了。他們向來都是戴有多副人格面具,到什麼山上唱什麼歌的。至於所謂“良心責備”,那就只有天公地母知道了,於人事何干?你同這類人講什麼“天地良心”,縱不是與虎謀皮,也無異於夏蟲語冰、對牛彈琴了。
“那麼,是非自有公論,公道自在人心。你李光地可以不在乎陳夢雷,也可以不去管什麼“天地良心”,難道就不怕社會輿論、身後公論嗎?
那他也自有應對的辦法——反正是“死豬不怕開水燙”。厚起臉皮來,笑罵由人笑罵,好官我自爲之。有道是:“身後是非誰管得”?“青史憑誰定是非”?
“私誼、公論全不在乎,身後是非也儘可拋開不管,對付這樣的人也真是毫無辦法。不過,能夠直接決定他的命運的康熙皇帝怎麼看他,那他還得認真考慮吧?康熙老佛爺可是眼睛裏揉不進沙子的。”
康熙皇帝精於世事,這不假,但他也要分別情況。對於這類“狗咬狗”的瑣事,他老人家纔不會作興去管哩!在這個雄鷙、精明的最高封建統治者眼裏,漢族官員都是一些奴才胚子,一些只供驅使的有聲玩具,是無所謂“義”,無所謂“德”的。恨不得他們一個個鬥得像烏眼雞似的纔好哩!互相攻訐,彼此監控,那就更容易加以駕馭、鉗制了。
本來,對於李光地的心術、品行,萬歲爺也好,一般僚屬也好,上上下下都看得十分清楚,“若犀燃鏡照而無遁形”。全祖望說得更是直截了當:“榕村(李光地號)大節,爲當時所共指,萬無可逃者”。可是,由於皇帝的百般迴護,儘管告訐、揭發者不乏其人,他還是仕途順暢,一路綠燈,後來以七十七歲高齡卒於任所。康熙帝深情悼惜,無限感傷地說:“知之最真無有如朕者,知朕者也無有過於李光地者。”雍正帝對他也十分賞識,即位之前即曾親筆賜贈“昌時柱石”的匾額,表彰李光地的勞績;登基後,在日理萬機的劬勞之餘,還記懷着已經作古多年的李光地,特予追贈太子太傅,並恩准其入祀賢良祠。
原來,在這些封建帝王腦子裏,社會倫理學是服從於現實政治需要的。他們所關心的是,你是否效忠於朕躬本身,是否效忠於大清王朝,你爲扞衛“家天下”的帝統和鞏固皇權做出過什麼貢獻,是否算得上一個夠格的忠順奴才。在這方面,應該承認,李光地是無可挑剔的。連陳夢雷都曾對康熙帝說過:李光地雖然愧負友人,但“千般萬般,要說他負皇上卻沒有”。對於李光地來說,只這一句話就夠了,等於加上了千保險、萬保險。這也就無怪乎康熙皇帝對這位“真忠臣也”,恩波浩蕩,褒賞有加了。從這兒也可以看出陳夢雷的忠厚而憨直的書生本色。這樣的“直巴頭”來和八竅玲瓏、鬼精鬼詐的李光地過招兒,自然是“孔夫子搬家——淨是書(輸)了”!你看人家李光地怎麼說他:“自甘從逆”,“辜負皇恩”。專揀要害的地方叼,用語不多,卻字字着硬。
不算結尾
西哲“讀史使人明智”的說法,無疑是正確的。不過,我覺得,還可以從另外一個視角來切入。讀史,也是一種今人與古人的靈魂的撞擊,心靈的對接。俗話說,“看三國掉眼淚——替古人擔憂”。這種“替古人擔憂”,其實正是讀者的一種積極參與和介入,而並非以一個冷眼旁觀者的姿態出現。它既是今人對於古人的叩訪,審視,駁詰,清算,反過來也是逝者對於現今還活着的人的靈魂的拷問,拉着他們站在歷史這面鏡子前照鑑各自的面目。在這種重新演繹人生的心路歷程中,只要每個讀者都能做到不僅用大腦,而且還能用心靈,切實深入到人性的深處,靈魂的底層,滲透進生命的體悟,那麼,恐怕就不會感到那麼超脫,那麼自在,那麼輕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