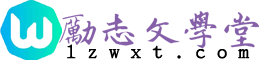巴金:化雪的日子
巴金:化雪的日子

初春的微風吹拂着我的亂髮,山腳下雪開始融化了。
化雪的日子是很冷的。但是好幾天不曾露臉的太陽在天空出現了。我披上大衣沐着陽光走下山去。
寂靜的山路上少有行人。雖然這裏只是一個小小的山坡,離城市又近,但是平日上山的人並不多。住在山上的人似乎都少有親友。他們除了早晨下山去買點飲食雜物外,便不大跟山下的人往來。山居是非常清閒的。
我因爲神經衰弱,受不了城市的喧囂,兩個月前便搬到山上來。在這裏生活很有秩序。一天除了按照規定的時間吃飯睡覺外,不做什麼事情。我喜歡一個人在山路上散步,但是有時候我也喜歡下山去找朋友談閒話。在這沒有一點波濤的安靜的山居中,我的身體漸漸地好起來了。
身體一好,精神也跟着好起來。心裏很高興。我覺得心裏充滿了愛:我愛太陽,愛雪,愛風,愛山,我愛着一切。
充滿了這種愛,我披上大衣踏着雪沐着陽光走下山去。
山路上積着雪,還沒有融化,不過有了好些黑的腳印。我愈往下走,看見腳印連起來,成了一堆一堆的泥淖。我愛聽皮鞋踏在雪上的聲音,總擇了雪積得最厚的地方走。沐着陽光,迎着微風,我覺得一個溫暖的春天向着我走來了。
我走了一半的路程,剛剛在一所別墅門前轉了彎,便看見一箇中國女人迎面走來。我一眼就認識她,站住叫了一聲“景芳”。我知道她是上山來找我的。
景芳正埋着頭走路,聽見我的聲音,擡起頭,答應一聲,急急跑過來。
她跑得氣咻咻的,臉上發紅。她一把抓住我苦惱地說:“我實在受不下去了。”
我看她這樣子,聽她這口氣,我不用問便知道她又跟她丈夫吵架了。我想我又得花費半天工夫去勸她。
“好,到我家裏去坐坐吧,”我微微皺着眉頭對她說。我陪她往上山的路走去。
她跟着我走。在路上她不開口了,我看見她依舊紅着臉,嘟起嘴在生氣,時時把皮鞋往雪上踢,彷彿肚裏有很多怨氣不曾吐出來。這一次他們一定吵得很厲害。我心裏想:他們夫婦像這樣生活下去是不行的。我也看得出來,他們吵架的次數愈多,兩個人中間的裂痕也就愈大了。
他們的吵架跟平常夫婦間的吵架是不同的。在他們中間從不曾發生過打罵的事情,最常有的是故意板起面孔或者一個人生自己的氣給對方看,使對方受不住。有時候他們也針鋒相對地辯論幾句,但是其中的一個馬上就跑開了,使這場爭吵無法繼續下去。
這樣的事情我看得多了。每次,妻子和丈夫都先後到我這裏來訴苦。我照例跟他們談很久,等他們氣平了才送出去。但是我始終不知道他們爲了什麼事情吵架。據我看來,他們好像是無緣無故地吵着玩。
說他們是一對愛吵架的夫婦吧,可是兩個人的脾氣都不壞,都是有教養而且性情溫和的人。就拿每次的吵架來說,起初每人對我說幾句訴苦的話,以後就漸漸地歸咎到自己,怪自己的脾氣不好,不能夠體諒對方。女的說這種話的時候常常眼裏含了淚,男的卻帶着一副陰鬱的面容。有時他們吵了架以後在我這裏遇見了,丈夫便溫柔地伴着妻子回去。
他們吵架的次數漸漸地多起來,就如同做過的事情又來重做。表面上總不外乎那一套把戲。但是它卻把我的腦子弄得糊塗了。我想在這簡單中一定隱藏着複雜。事情決非偶然發生,一定有特別的原因。我想把原因探究出來。
我曾研究過他們兩人的性情,但是我不能夠看得很清楚。女的似乎熱情些,男的似乎更冷靜。女的活潑些,男的卻比較嚴肅。不過這也只是表面的觀察。
我同這對夫婦的交情不算深,因爲認識的時間還不久。但是因爲同住在外國,又在鄉間,環境使我們成了親密的朋友。不過對於他們的過去生活我依舊不很清楚。我只知道他是中等官僚的兒子,夫婦兩人都是大學生。他們是由自由戀愛而結合的,那是三年前的事情。可是到現在他們還沒有一個小孩。
據我看來在他們中間並沒有什麼障礙。他們應該過得很好。感情好。經濟情形好。兩個人都在讀書:男的研究教育,女的研究文學,這也不會引起什麼衝突。
我始終找不出他們夫婦吵架的真正原因。這一次也找不到一點線索。她的嘴老是閉着。嘴上憤怒的表情卻漸漸地淡起來。她走到我家時,她的怒氣已經平靜下去了。
“什麼事情?是不是又吵了架?”我讓她進了屋,脫下大衣,把她的和我自己的大衣都掛在衣架上,一面不在意地問她道。
她點點頭,頹喪地在沙發上坐下來,用手摸她的頭髮,呆呆地望着牆上的一幅畫。
“爲着什麼事情?”我坐在她對面,看見她不說話,便又追問了一句,我注視着她的臉,不讓她逃避。
“什麼事情?”她微微笑了,她顯然是拿微笑來掩飾心中的憂鬱。她看我一眼,又把眼睛擡上去,做夢般地看牆上的那幅畫。頭靠在沙發背上,兩手託着頭,自言自語地說下去:“老實說,沒有什麼事情。我自己不知道應該怎樣做。我想我們這樣住下去是不行的。……我們也許應該分開。”
“分開”?我聽到這兩個字心裏吃一驚。我暗中觀察她的態度。她是在正經地說話,帶着憂愁的神氣,卻沒有一點憤怒。我想她這句話決不是隨便說出來的。她至少把“分開”的事情先思索了一番。
“分開”的確是一個解決爭吵的辦法。但是到了提出“分開”的問題的地步,事情一定是很嚴重的了。我心裏發愁,老實說,我很不願意讓這一對年輕夫婦分開,雖然我也不願意看見他們常常吵架。
“分開?”我微微把眉頭一皺,連忙陪笑說:“不要扯得太遠了。夫婦間小小的爭吵也是很平常的事情,只要大家讓步,就容易和平解決。我看你們應該是一對很合理想的夫婦。”
“我原也是這樣想。”她低聲嘆了一口氣,惋惜地說了這句話。歇了片刻才接着說下去:“可是事實上不是這樣。我也不知道爲什麼,總之我們中間有一種障礙。”
“障礙?什麼障礙呢?”我驚訝地問道。我彷彿發見了一件新奇的東西。
“我也不知道。”她絕望地回答。“這是無形的,我也看不出來,但是我總覺得……”她閉了嘴慢慢地咬着嘴脣皮,我看出來那似乎是淺淡而實在是深切的苦惱像黑雲一般籠罩了她的美麗的臉龐。尤其是那一對眼睛,裏面盪漾着波濤,我觸到那眼光,我的心也開始沉下去了。
“茲生,你一定給我想個辦法。我沒有勇氣再跟他一起住下去了。”她求助般地對我說。
我陷在十分困難的境地中了。我這時候很同情她,很願意幫助她,但我又是她丈夫伯和的朋友,而且我實在看不出他們應該分開的理由。那麼我應該爲她想個什麼樣的辦法呢?我又不是一個頭腦靈活的人。
“我問你究竟還愛不愛他?”我想了半天才想到這句話,我這時候只希望他們兩個能夠和好起來。
“我愛他。”她略略停頓一下便肯定地回答道。我看她的臉,她臉上開始發亮了。我明白她的確說了真話。
這個回答頗使我高興。我以爲問題不難解決了。我直截了當地說: “那麼你還說什麼分開的話?你既然愛他,那麼一切都不成問題了。”
“可是他——”她遲疑地說了這三個字。
“他,難道伯和不愛你!不,我想他不會!他又沒有別的女朋友,”我帶着確信地說。我看見話題愈逼愈近,很想趁這個機會給她解說明白,也許可以從此解決了他們夫婦的爭端。
“我不知道。他從前很愛我。現在他不像從前那樣了。有時熱,有時又冷淡。他常常無緣無故地做冷麪孔給我看。譬如今天早晨我興致很好地要他一起上山來看你,他不理我,卻無緣無故地跟我生氣。從前我只要一開口,他就會照我的意思做。現在他常常半天不理我,只顧讀他的書,或者一個人跑出去,很晚纔回家來。他這種態度我受不了。……也許這要怪我脾氣不好,我不能夠體諒他。我也知道。可是……”她說話時聲音很平靜,這表示她的腦子很清楚,並不曾被感情完全矇蔽。但是憂慮使她的聲音帶了一點點顫動,方纔在她的臉上出現過一次的亮光已經滅了。她的眼睛裏包了一汪淚。我細看她的神情,的確她怨她自己甚於怨她的丈夫。
我的心越發軟下來了。我想伯和不應該這樣地折磨她。他爲了什麼緣故一定要使她如此受苦呢?說他不愛她吧,但是從一些小的動作上看來,他依舊十分關心她,愛護她。說他別有所愛吧,但是他並沒有親密的女朋友。他們的生活並沒有什麼變動。那麼是什麼東西站在他們的中間,阻止他愛她呢?她所說的無形的障礙究竟是什麼呢?我很想知道這個,然而我卻不能夠知道。至少從她這裏我是無法知道的。我只得拿普通的道理來勸她: “景芳,不要把事情看得太認真。我想你一定對伯和有誤會。伯和決不是那樣的人。而且夫婦間吵架,不過是爭一時的閒氣,我擔保過一會兒你們就會和好起來。”
“茲生,你不知道當初他對我多麼好,真是好得很。體貼,愛護,敬重,無微不至。所以爲了愛他,我甘願離開我的家庭,跟着他遠渡重洋。可是現在……我知道我在他的心上已經佔不到重要位置了。”她惋惜地說下去。她完全不注意我的話。我也明白我的道理太平凡了。這樣的話我對她說過好幾遍,說了跟沒有說一樣。
“茲生,你不知道,你不知道。往事真不堪回首。”她漸漸地激動起來,彷彿感情在鼓動她,她無法抑制了。她的話裏帶着哭聲,同時她拿了手帕在揩那正從她的眼角落下來的淚珠。 我的困窘一秒鐘一秒鐘地增加。我找不出話安慰她。但是看見她默默地抽泣的樣子,就彷彿也有悲哀來攪亂我自己的心。壁爐裏火燃得正旺,不斷地射出紅藍色的光。窗帷拉開在旁邊,讓金色的陽光從玻璃窗斜射進來,照亮了我面前的書桌。我的上半身正在陽光裏。房裏很溫暖,很舒適。然而我的心卻感覺不到這些。我只希望伯和馬上就到這裏,把我從這樣一個困難的境地裏救出來。我知道這個希望很有成爲事實的可能。
不久伯和的頎長的影子就在我的窗前出現了。他走得很慢,腳步似乎很沉重。兩三天不見面,這個人顯得更陰鬱了。
他進了房間,照例脫了大衣,招呼我一下,不說別的話,便走到他妻子面前。她依舊坐在沙發上,埋着頭用手帕遮住眼睛。她知道他來,也不理他。
他在沙發的靠手上坐上,愛撫地摩她的肩頭,低聲在她耳邊說:“景芳,回去吧。”她不答應。他接連說了三次,聲音更溫和。她含糊地應了一聲。
“我們回去吧。不要在這裏打擾茲生了。這一次又是我不好。”他站起來輕輕地拉她的膀子,一面埋下頭在她的耳邊說話。
我明白我留在房裏對他們不方便,就藉故溜出去了,並不驚動他們。我不知道他們在房裏說了些什麼話。等我回到房間裏的時候,他正挽着她準備走了。兩個人臉上都帶着笑容。又是一個照例的喜劇的結局。
我祝福他們,把他們送走了。心裏想,在這次的和解以後,他們夫婦總可以過五天安靜的日子吧。
但是就在這天晚上伯和一個人忽然跑到我這裏來。時間不早了。外面吹着風。院子裏牆邊還堆着未融化的雪。我剛剛讀完了一部傳記,爲書中的情節和文筆所感動,非常興奮,一個人坐在沙發上對着燈光空想些不能實現的事情。門鈴忽然響了。我已經聽見了伯和的腳步聲。我不安地想,大概在他們夫婦中間又發生了爭端。我去給他開了門。
他的一張臉凍得通紅。他脫下大衣,便跑到壁爐前面,不住地搓着手躬着身子去烤火。我默默地看他的臉,壁爐裏的火光映在他的臉上,使他顯得更爲陰森可怕,比風暴快來時候的天空還要可怕。
我的不安不斷地在增加。我很想馬上知道他的臉所暗示的風暴究竟是怎麼一回事,但是又擔心這風暴會來得太可怕,我會受不住。因此我便閉上嘴等待着,雖然這等待的痛苦也很令人難堪。
他轉身在房裏走了兩步,忽然猛撲似的跑到我身邊,抓住我的左膀,煩躁地說:“茲生,你幫助我!”
我驚愕地望着他,他的一對眼睛圓圓地睜着,從臉上突出來,彷彿要打進我的眼裏似的。是那麼苦惱的眼光!我被它看得渾身起了顫慄。
“什麼事情?告訴我。”我吃驚地問。在窗外風接連敲着窗戶。寂靜的院子裏時時起了輕微的聲音,彷彿有人走路,彷彿有人咳嗽。
“茲生,我不能夠支持下去了。你說,你說應該怎麼辦!我對景芳……”他放鬆了我的左膀,絞着自己的手指,直立在我面前。
提起景芳,我馬上想到了那個穿青色衫子腰間束紅帶的面孔圓圓的女人,我想到了這一天她一邊流淚一邊訴說的那些話。我的心軟下來了。同情抓住了我。我溫和地拍他的肩膀,對他說:“你坐下吧。我們慢慢地說。”我替他拉了一把椅子放在我對面離壁爐不遠處,讓他坐下來。我們對面坐着,我不等他開口便先說道:“伯和,你不應該這樣折磨景芳。她至今還愛你。你爲什麼老是跟她吵架?你說讓她一點兒也是應該的。況且她的脾氣並不壞。”我的態度和聲音都是非常誠懇的。我想這番話一定會使他感動。
他不住地眨眼,動嘴,但是他等到我說完了才搖搖頭絕望地說:“你不瞭解我們的情形。” “那麼是誰的錯?難道還是她的錯?”我看見他不肯接受我的意見,一句話就拒絕了它,因此不高興地說了上面的類似質問的話。
我的話一定使他很難堪,他的臉色馬上變得更難看了。過了一會兒他才痛苦地回答道: “那自然是我的錯,我也承認。她沒有一點錯。”這答語雖然是我意料不到的,但是我卻高興聽它。我想抓住這一點,我就可以解決他們的爭端了。我便追問下去: “你究竟爲什麼一定要那樣做?你既然知道自己錯了,難道就不可以從此改過來?”
他並沒有感激和欣悅的表情,他只是絕望地搖着頭,困惱地說:“你還是不瞭解。”
這句話把我弄得更糊塗了。我簡直猜不透他的心思。窗外風依舊低聲叫喚。爐火燃得正旺,可怕的火光映紅了我們兩人的臉。他的臉像一個解不透的謎擺在我眼前。
“我現在嚐到愛的苦味了。”他自言自語地嘆息說。他埋下頭,兩手矇住臉,過了一會兒纔再擡起頭來。我知道他是默默地在讓痛苦蠶食他的心;我知道他的痛苦是大於我所想象的。因此我也不能夠用隔膜的語言去探詢他了。
“茲生,相信我,我說的全是真話。”他開始申訴般地說。“我的確愛過景芳,到現在還愛她。我也知道她還在愛我。然而——”他停了停,沉思般地過了片刻,這時候他把一隻手壓在額上。我也注意他的前額。我看見他額上已經掛滿汗珠了。
“然而我不願意再愛她了。”他突然放下手急轉直下地說,態度是很堅決的,彷彿愛給他帶來了很大的痛苦。“愛是很痛苦的。從前她也曾使我快樂,使我勇敢。然而那些日子已經過去了。那愛撫,那瑣碎的生活我不能夠忍受。你知道我的思想變了……”
我只顧惶惑地望着他,他說的我全不知道。我不瞭解,但是我相信他的話是真實的。
“我有了新的信仰,我不能夠再像從前那樣地過日子。我要走一條跟從前的相反的新路,所以我要譭棄從前的生活。”
他像朗誦一般說着這些話,可是我依舊不能夠了解。他繼續說下去: “然而她卻不能夠往前走了。她不贊成我的主張。她要過從前的生活。這也許不是她的錯。……然而她卻使我也留戀從前的生活。她愛我,她卻不瞭解我的思想,她甚至反對它。現在是她使我苦惱,使我遲疑了。”
他嘆了一口氣。我注意到他說起“她”字時依舊帶着愛撫的調子。他雖然說了這些對她不滿的話,但是他這時候明明還愛她。這件事情更奇怪了。
“要是她不愛我吧,那倒好辦了。然而……我說要拋棄現在有的一切,我要回國,我還要……然而你想她能夠忍受嗎?她能夠讓我做嗎?‘離開她吧!離開她吧!’彷彿有一個聲音天天在我耳邊這樣說,然而——”
他的這幾個“然而”把我弄得更糊塗了。但是我望着他那張被深的苦惱籠罩着的臉,聽着他用顫抖的聲音說出來的奇怪的話,我漸漸地對他抱了同情。同時那個女人的面影卻漸漸地淡了下去。
“我天天下了決心,我天天又毀了這個決心,都是爲了她!爲了愛她!使我長久陷在這種矛盾的生活裏。我不能夠再支持下去了。我起了拋棄她的念頭。然而我沒有膽量。永遠是爲了愛她!我跟她吵過架,然而過了一會兒我又不能自持地求她原諒了。愛把我的心抓得這樣緊!” 他不甘心地吐了一口氣,伸手在胸膛上胡亂抓了一把,好像要把愛從那裏面抓出來一樣。
“我最後想到一個辦法。我想只有讓她離開我。於是我故意把自己變成一個殘酷無情的人,常常無緣無故地跟她爭吵,這只是爲了使她漸漸地對我失望,對我冷淡,使她不再愛我,使她恨我……”
他突然閉上嘴,現出呼吸困難的樣子,把一張臉擺在我跟前,他的臉越發黑了,在那上面我看不見一線的希望。只有在那雙眼睛裏燃燒着一種可怕的東西。就在這個時候,就在這種情形下面,我明白了他們爭吵的原因,我看穿了那個謎,但是反倒使我陷在更困難的境地裏了。
“我用了這個辦法,我折磨我自己,我折磨她。我殘酷地吞食了她的痛苦。我全明白。她全不知道。然而這也沒有用,只給我帶來更多的痛苦。她依舊愛我。她從不會起分開的念頭。所以我到底失敗了。每一次吵架以後我總要安慰她。她使我變得這樣懦弱!我簡直無法跟她分開!”
他的絕望的呼號在房裏微弱地抖動着,沒有別的聲音來攪亂它。在外面風歇一陣又猛烈地刮一陣。房裏漸漸地涼起來。我走到壁爐前加了些柴和炭進爐裏。我沒有說話,但是心裏老是想着爲什麼他一定要跟她分開。
“然而這樣下去是不行的。我必須跟她分開,使她去愛別人。然而我又不能夠。茲生,我不能夠支持下去了。我不能夠裝假了。我想不到愛會使我這樣地受苦。我不要愛!我不要愛!……”
他絕望地抓他的胸膛,好像他已經用盡一切的方法了。他不等我回答就站起來,走到那張大沙發跟前,坐下去,把臉壓在沙發的靠手上。
房裏靜得可怕。外面的風倒小了。柴在壁爐裏發出叫聲。空氣壓得人透不過氣。我的心被痛苦和恐怖糾纏着,這一晚的安寧全給伯和毀掉了。但是我不怨他,反而因爲他的苦惱我也覺得苦惱了,雖然我並不瞭解爲什麼愛一個女人卻不得不引起她的恨。
“伯和,既然這樣,你爲什麼一定要斷絕她的愛,一定要跟她分開?你們就不可以再像從前那樣和好地過日子嗎?你應該仔細地想一下!”我終於掉轉身子對他溫和地勸道。
他一翻身站起來,眼睛非常乾燥。他爭辯地說:“這不行!這不行!我要回國去!我有更重要的事情!我不能再留在這裏過這種矛盾的生活!……”他絞着手踱了幾步,突然跑過來,抓起我的膀子,激動地說:“茲生,我告訴你:我們打掉了一個孩子。現在是第二個了。她不肯。這一次她一定不肯。你想我應該怎麼辦?”他的眼光逼着我,要我給他一個回答。
這番話來得很突然,很可怕,我從前完全不知道。但是現在我卻更同情景芳而更不瞭解他了。我甚至覺得他的舉動太不近人情,我便帶了點氣憤地說:“她的意思是對的。這是她的權利,你不能夠強迫她。”
“然而這也不是我的錯。我們都是犧牲者。”他並不因爲我的話生氣,他只是這樣辯解道,他的聲音漸漸溫和,不像先前那樣地激動了。“我自己也是很痛苦的,我的痛苦比她的一定還要厲害。茲生,我希望你瞭解我,我並不是一個不近人情的人。我也是不得已的。你看我掙扎得多麼痛苦!我簡直找不到一個人來聽我訴苦!只有你!景芳完全不瞭解我。我不能夠對她說明白。”他最後嘆了一口氣自語說:“我現在嘗夠了愛的苦味了。”他把身子伸直起來默默地站在我面前,好像要使我看明白這個頎長的身子裏裝了多大的痛苦。
聽見他這些話,我越發莫名其妙了。我也是一個遇事不能決斷的人,一個懦弱的人。我時而同情景芳,時而同情伯和。我很早就想找一個辦法來解決他們夫婦的爭端,可是如今伯和懷着這麼痛苦的心來求助於我,我卻毫無辦法了。我只是困惱地在我的枯窘的思想中找出路。 “茲生,我問你,你老實說:你喜歡景芳嗎?”他默默地踱了一陣,忽然帶着一種異樣的表情,走到我身邊,用顫抖的聲音對我說了上面的話。
我茫然地點着頭。我的確喜歡景芳,而且自從他給了她這許多苦惱以後我更同情她了。我看見他的眼睛忽然亮起來,他臉上的黑雲也有些開展了。我的點頭會使他這樣地滿意,我想不到。但是一瞬間一個思想針一般地刺進我的腦子。我恍然地明白他的心思了。我像受了侮辱般地跳起來,氣憤地責備說:“你會有這種思想!真是豈有此理!”我對着他的臉把話吐過去。 他退了兩步,憂鬱地微笑了。他分辯道:“你爲什麼要生氣?我是出於真心。我並不是疑惑你。”
“你去掉這種古怪思想吧。我勸你還是回家去同景芳好好地過日子,不要自尋煩惱了!”我壓下怒氣最後勸他道,我疑心他要發狂了。
這一下又使他突然沉下臉來。他頹喪地落在沙發裏埋下頭坐了半晌。於是他站起來,失望地說:“我走了。”便拿起大衣披在身上開門走了。
我沒有留他,默默地跟着他站起來,走到門口。他把門一拉開,一股冷風吹入,我不覺打了一個寒噤。我耳裏只聽見風聲。我想挽留他,但是他賭氣走了。
我心裏很難受,覺得不該這樣對待他。我知道他是懷了絕大的痛苦來求助於我,我卻給他添了更多的痛苦把他遣走了。
我懊惱地走回到沙發前面,坐下去,無意間擡起頭,看見了牆上那幅題作《母與子》的名畫,就是景芳今天常常看的那幅,畫上一個貴婦人懷裏抱了一個兩歲多的男孩。這又使我想到景芳的生活,使我越發同情她,使我爲她的處境感到苦惱。但是一想到伯和的那個古怪的念頭,我馬上又把景芳的影像趕出我的腦子去了。
這個晚上我沒有睡好覺,而且做了奇怪的夢。第二天我很遲纔起來,覺得頭昏。我勉強支持着下山去看伯和夫婦。
天氣很好,溫和的太陽照着山路,雪除了幾處凍在樹腳和牆邊的以外都化盡了。路是乾燥的。我扶着手杖慢慢地走着。下了山到了伯和夫婦的家。
伯和病在牀上,景芳在旁邊照料他。他們露出比往日更親密的樣子。
伯和的病很輕,景芳說是因爲他昨晚在外面喝醉酒,冒着風到處跑了半夜而起的。她似乎不知道他曾清醒地到過我家談了那許多話。他一定不曾告訴她。現在躺在病牀上他更容易哄騙她了。其實不僅是她,便是我,看見他對待她的神情,我也疑心他昨夜是不是到我家去過。 我自然爲他們夫婦的和好感到欣慰。我在他們家裏停留片刻。他絕口不提昨晚的事情,一直到我告辭的時候,我還看見他的臉上帶着溫和的微笑。
我回到家裏,仔細地想着這一對夫婦間的種種事情。我想解決那個謎,但是愈想下去愈使我糊塗。我的頭在痛了。
我的神經受到這些刺激以後身體又壞下去。我在家裏躺了十幾天不能夠出門。等我病好拄着手杖下山的時候,已經是晴朗的仲春天氣了。
伯和夫婦並不曾來看過我的病。在我的病快好的時候我接到他們兩個署名的一封信,是從馬賽寄發的,說他們已經買了船票,就要動身回國了。
以後我就沒有得過他們一封信,我不知道他們在國內幹些什麼事情。只是在我感到寂寞而無法排遣的時候,我還常常想起這對年輕的夫婦,還誠心地祝福他們。
四年以後的夏天,我在法國南部海邊的一個城裏過暑假。
我常常到海邊去洗澡,躺在沙灘上曬太陽。在這裏只有幾個中國人。因此我有一天在沙灘上碰見的一對帶着一個男孩的中國夫婦引起了我的注意。
這對夫婦剛從水裏出來,還穿着浴衣,女的手裏牽着孩子,走到一把傘下面躺下了。她在跟孩子講話。我看見那個女人的身材和相貌很像我的一個熟朋友,連聲音也像是熟人的聲音。我好奇地走過去看她。她正無意地掉過頭來,我看清楚了她的面龐,不覺驚喜地叫道:“景芳!”
那個女人連忙跳起來,跑到我身邊,高興地叫着:“茲生!原來是你,想不到你還在這裏!”她含笑地緊緊捏住我的手。
她沒有什麼改變,只是人更健壯些、活潑些、快樂些。
“你們是什麼時候來的?爲什麼不給我一個信?那是你們的孩子嗎?”我快活地望着她的健康色的臉接連地問道。我又指着那個男孩,他正向我們跑來。
“兩個多月了。來這裏不過幾天。讓我帶寶寶來看你。”她迴轉身去接了他來,要他招呼我,給我行禮,這是一個四歲的孩子,很像他的父親,尤其是一張嘴和一對眼睛。
我拍了拍他的肩頭,說了兩句話,想起他的父親來,很奇怪,伯和爲什麼不過來招呼我,卻躲在傘下面睡覺,便說:“我們看伯和去!”
她不說什麼,陪着我走到傘旁邊。那個男子馬上站起來迎接我們。一個完全陌生的面孔。我癡癡地站在他面前,不知道應該怎樣做。
“這是我的丈夫。”景芳在旁邊介紹說,她還說出了那個人的姓名,可是我卻沒有心思聽了。
我說了幾句應酬話,就告辭走了。我要求景芳陪我走幾步,她沒有拒絕。在路上我問她伯和的消息,她說不知道。她不肯說一句關於伯和的話。我問她伯和是不是還在這個世界上,她也說不知道。但是我暗暗地注意她的臉部表情,我知道她這時心裏很痛苦,我也不再追問,就跟她分別了。
那個男子是年輕的、溫和的、健壯的、頎長的。景芳同他在一起大概過得很幸福。我想,不管伯和是活着或者已經死亡,假若他能夠知道景芳現在的生活情形,他一定很放心,而且他的目的也已經達到了。
1934年秋在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