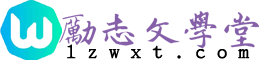懷念父親到心碎的散文
懷念父親到心碎的散文

導語:父愛是一座高山,支撐起一片蔚藍的藍天;有人說,父愛是一片天,他比地還大,比海還闊!而在我心中父愛是一杯淡淡的清茶,它沒有任何香料的摻加,僅有濃濃的愛意,這就是父愛,父愛大於世界上的任何東西!!這裏本站的小編爲大家整理了三篇懷念父親到心碎的散文,希望你們喜歡。

一、《我的啞巴父親》
遼寧北部有一箇中等城市,鐵嶺,在鐵嶺工人街街頭,幾乎每天清晨或傍晚,你都可以看到一個老頭兒推着豆腐車慢慢走着,車上的蓄電池喇叭發出清脆的女聲:“賣豆腐,正宗的滷水豆腐!豆腐咧——”那聲音是我的。那個老頭兒,是我的爸爸。爸爸是個啞吧。直到長到二十幾歲的今天,我纔有勇氣把自己的聲音放在爸爸的豆腐車上,替換下他手裏搖了幾十年的銅鈴兒鐺。
兩三歲時我就懂得了有一個啞吧爸爸是多麼的屈辱,因此我從小就恨他。當我看到有的小孩兒被媽媽使喚着過來買豆腐卻拿起豆腐不給錢不給豆兒就跑,爸爸伸直脖子也喊不出聲的時候,我不會像大哥一樣追上那孩子揍兩拳,我傷心地看着那情景,不吱一聲,我不恨那孩子,只恨爸爸是個啞吧。儘管我的兩個哥哥每次幫我梳頭都疼得我呲牙咧嘴,我也還是堅持不再讓爸爸給我扎小辮兒了。媽媽去世的時候沒有留下大幅遺像,只有出嫁前和鄰居阿姨的一張合影,黑白的二寸片兒,爸爸被我冷淡的時候就翻過支架方鏡的背面看***照片,直看到必須做活兒了,才默默地離開。
最可氣的是別的孩子叫我“啞吧老三”(我在家中排行老三),罵不過他們的時候,我會跑回家去,對着正在磨豆腐的爸爸在地上劃一個圈兒,中間唾上一口唾沫,雖然我不明白這究竟是什麼意思,但別的孩子罵我的時候就這樣做,我想,這大概是罵啞吧的最惡毒的表示了。
第一次這樣罵爸爸的時候,爸爸停下手裏的活兒,呆呆地看我好久,淚水像河一樣淌下來,我是很少看到他哭的,但是那天他躲在豆腐坊裏哭了一晚上。那是一種無聲的悲泣。
因爲爸爸的眼淚,我似乎終於爲自己的屈辱找到了出口,以致以後的日子裏,我會經常跑到他的跟前去,罵他,然後顧自走開,剩他一個人發一陣子呆。只是後來他已不再流淚,他會把瘦小的身子縮成更小的一團,猥在磨杆上或磨盤旁邊,顯出更讓我瞧不起的醜陋樣子。
我要好好唸書,上大學,離開這個人人都知道我爸爸是個啞吧的小村子!這是當時我最大的願望。我不知道哥哥們是如何相繼成了家,不知道爸爸的豆腐坊裏又換了幾根新磨杆,不知道冬來夏至那磨得沒了沿鋒的銅鈴鐺響過多少村村寨寨……只知道仇恨般地對待自己,發瘋地讀書。
我終於考上了大學,爸爸頭一次穿上1979年姑姑爲他縫製的藍褂子,坐在1992年初秋傍晚的燈下,表情喜悅而鄭重地把一堆還殘留着豆腐腥氣的鈔票送到我手上,嘴裏哇啦哇啦地不停地“說”着,我茫然地聽着他的熱切和驕傲,茫然地看他帶着滿足的笑容去通知親戚鄰居。當我看到他領着二叔和哥哥們把他精心飼養了兩年的大肥豬拉出來宰殺掉,請遍父老鄉親慶賀我上大學的時候,不知道是什麼碰到了我堅硬的心絃,我哭了。吃飯的時候,我當着大夥兒的面兒給爸爸夾上幾塊豬肉,我流着眼淚叫着:“爸,爸,您吃肉。”爸爸聽不到,但他知道了我的意思,眼睛裏放出從未有過的光亮,淚水和着散裝高梁酒大口地喝下,再吃上女兒夾過來的肉,我的爸爸,他是真的醉了,他的臉那麼紅,腰桿兒那麼直,手語打得那麼瀟灑!要知道,十八年啊,十八年,他從來沒見過我對着他喊“爸爸”的口型啊!
爸爸繼續辛苦地做着豆腐,用帶着豆腐淡淡腥氣的鈔票供我讀完大學。1996年,我畢業分配回到了距我鄉下老家40華里的鐵嶺。
安頓好了以後,我去接一直單獨生活的爸爸來城裏享受女兒遲來的親情,可就在我坐着出租車回鄉的途中,車出了事故。
我從大嫂那裏知道了出事後的一切——過路的人中有人認出這是老塗家的三丫頭,於是腿腳麻利的大哥二哥大嫂二嫂都來了,看着渾身是血不省人事的我哭成一團,亂了陣腳。最後趕來的爸爸撥開人羣,抱起已被人們斷定必死無疑的我,攔住路旁一輛大汽車,他用腿扛着我的身體,騰出手來從衣袋裏摸出一大把賣豆腐的零錢塞到司機手裏,然後不停地划着十字,請求司機把我送到醫院搶救。嫂子說,一生懦弱的爸爸,那個時候,顯出無比的堅強和力量!
在認真地清理傷口之後,醫生讓我轉院,並暗示哥哥們,我已沒有搶救價值,因爲當時的我,幾乎量不到血壓,腦袋被撞得像個癟葫蘆。
爸爸扯碎了大哥絕望之間爲我買來的喪衣,指着自己的眼睛,伸出大拇指,比劃着自己的太陽穴,又伸出兩個手指指着我,再伸出大拇指,搖搖手,閉閉眼,那意思是說:“你們不要哭,我都沒哭,你們更不要哭,你妹妹不會死的,她才20多歲,她一定行的,我們一定能救活她!”醫生仍然表示無能爲力,他讓大哥對爸爸“說”:“這姑娘沒救了,即使要救,也要花好多好多的錢,就算花了好多錢,也不一定能行。”爸爸一下子跪在地上,又馬上站起來,指指我,高高揚揚手,再做着種地、餵豬、割草、推磨杆的姿勢,然後掏出已經空的衣袋兒,再伸出兩隻手反反正正地比劃着,那意思是說:“求求你們了,救救我女兒,我女兒有出息,了不起,你們一定要救她。我會掙錢交醫藥費的,我會餵豬、種地、做豆腐,我有錢,我現在就有四千塊錢。”醫生握住他的手,搖搖頭,表示這四千塊錢是遠遠不夠的。爸爸急了,他指指哥哥嫂子,緊緊握起拳頭,表示:“我還有他們,我們一起努力,我們能做到。”見醫生不語,他又指指屋頂,低頭跺跺腳,把雙手合起放在頭右側,閉上眼,表示:“我有房子,可以賣,我可以睡在地上,就算是傾家蕩產,我也要我女兒活過來。”又指指醫生的心口,把雙手放平,表示:“醫生,請您放心,我們不會賴帳的。錢,我們會想辦法。”大哥把爸爸的手語哭着翻譯給醫生,不等譯完,看慣了生生死死的醫生已是淚流滿面。他那疾速的手勢,深切而準確的表達,誰見了都會淚下!
醫生又說:“即使作了手術,也不一定能救好,萬一下不來手術檯……”爸爸肯定地一拍衣袋,再平比一下胸口,意思是說:“你們盡力搶救,即使不行,錢一樣不少給,我沒有怨言。”偉大的父愛,不僅支撐着我的生命,也支撐起醫生搶救我的信心和決心。我被推上手術檯。
爸爸守在手術室外,他不安地在走廊裏來回走動,竟然磨穿了鞋底!他沒有掉一滴眼淚,卻在守候的十幾個小時間起了滿嘴大泡!他不停地混亂地做出拜佛、祈求天主的動作,懇求上蒼給女兒生命!
天也動容!我活了下來。但半個月的時間裏,我昏迷着,對爸爸的愛沒有任何感應。面對已成“植物人”的我,人們都已失去信心。只有爸爸,他守在我的牀邊,堅定地等我醒來!
他粗糙的手小心地爲我按摩着,他不會發音的嗓子一個勁兒地對着我哇啦哇啦地呼喚着,他是在叫:“雲丫頭,你醒醒,雲丫頭,爸爸在等你喝新出的豆漿!”爲了讓醫生護士們對我好,他趁哥哥換他陪牀的空檔,做了一大盤熱騰騰的水豆腐,幾乎送遍了外科所有醫護人員,儘管醫院有規定不準收病人的東西,但面對如此質樸而真誠的表達和請求,他們輕輕接過去。爸爸便滿足了,便更有信心了。他對他們比劃着說:“你們是大好人,我相信你們一定能治好我的女兒!”這期間,爲了籌齊醫療費,爸爸走遍他賣過豆腐的每一個村子,他用他半生的忠厚和善良贏得了足以讓他的女兒穿過生死線的支持,鄉親們紛紛拿出錢來,而父親也毫不馬虎,用記豆腐帳的鉛筆歪歪扭扭卻認認真真地記下來:張三柱,20元;李剛,100元;王大嫂,65元……
半個月後的一個清晨,我終於睜開眼睛,我看到一個瘦得脫了形的老頭,他張大嘴巴,因爲看到我醒來而驚喜地哇啦哇啦大聲叫着,滿頭白髮很快被激動的汗水濡溼。爸爸,我那半個月前還黑着頭髮的爸爸,半個月,老去二十年!
我剃光的頭髮慢慢長出來了,爸爸撫摩着我的頭,慈祥地笑着,曾經,這種撫摩對他而言是多麼奢侈的享受啊。等到半年後我的頭髮勉勉強強能紮成小刷子的時候,我牽過爸爸的手,讓他爲我梳頭,爸爸變得笨拙了,他一絲一縷地梳着,卻半天也梳不出他滿意的樣子來。我就扎着亂亂的小刷子坐上爸爸的豆腐車改成的小推車上街去。有一次爸爸停下來,轉到我面前,做出抱我的姿勢,又做個拋的動作,然後捻手指表示在點錢,原來他要把我當豆腐賣嘍!我故意捂住臉哭,爸爸就無聲地笑起來,隔着手指縫兒看他,他笑得蹲在地上。這個遊戲,一直玩兒到我能夠站起來走路爲止。
現在,除了偶爾的頭疼外,我看上去十分健康。爸爸因此得意不已!我們一起努力還完了欠債,爸爸也搬到城裏和我一起住了,只是他勤勞了一生,實在閒不下來,我就在附近爲他租了一間小棚屋做豆腐坊。爸爸做的豆腐,香香嫩嫩的,塊兒又大,大家都願意吃。我給他的豆腐車裝上蓄電池的喇叭,儘管爸爸聽不到我清脆的叫賣聲,但他是知道的,每當他按下按鈕,他就會昂起頭來,滿臉的幸福和知足,對我當年的歧視竟然沒有絲毫的記恨,以致於我都不忍向他懺悔了。
我常想:人間充滿了愛的交響,我們傾聽、表達、感受、震撼,然而我的啞吧父親卻讓我懂得,其實,最大的音樂是無聲,那是不可懷疑的力量,把我對愛的理解送到高處。
二、《一輩子陪伴》
我一直在思忖:要不要給父親打個電話,要不要呢?
父親一定是不在家的。他這時也許正站在5樓或者8樓的腳手架上奮力扔上了又一塊磚,擦一擦汗的工夫,就被人拼命地吆喝。十幾年了,人也上了50,不知道他,還受不受得了。
但父親是心甘情願又志得意滿的,至少他每次與我說話都在努力表達這樣的意思。而我,越發地不安。
我今年22歲了,父親52。我4歲時母親改嫁他鄉,父親和我磕磕絆絆地活着。多少年了,數也數不清楚,那些漫長的日子怎麼可以用一個數字說過來呢?
父親的智商比一般人要低一點,生活簡單得像幾條縱橫的網格。很早的時候,別人扔掉一架破木車,他撿回來,敲敲打打,然後拖着上路了,沿途把別人扔下的酒瓶廢鐵等破東西撿上車拖回家。時間久了,鄉鄰們也把不要了的東西放到他車上。我整天埋在那一堆破爛裏翻翻揀揀,窮人的孩子,六七歲就當了家。
冬天來的時候,我放錢的紙盒子已經有了沉甸甸的滿足。這年過年,我們吃了魚和肉。一個8歲的女孩子,把年夜飯看了又看,從心底裏微笑着叮囑自己記住那一刻龐大的快樂,所以,一直到現在,十多年過去了,也忘不了當時滿滿的幸福。
父親種的瓜菜都新鮮水嫩,我們兩個人吃得很少,我就把大部分放到父親的小推車上。鄉里鄉親的嫂子大娘誰要就從上面拿走,回去包頓餃子或者做頓湯麪,也不說謝,偶爾記得,差他們的孩子送一碗給我,我笑笑地接着,也不說謝。
吃百家飯穿百家衣,我沉默着、絢爛着,也成長着。每天最好的時光便是我踩在小凳上彎腰炒菜,父親坐在竈前燒火,不時驚慌地去扶一下我腳下的小凳,見很安全了,就呵呵笑起來。現在去想那段日子,總是首先憶起竈間的那片陽光,10歲左右的陽光,竟然是天長地久的樣子。
這樣的日子持續了多少年我已經不記得了。我用紙盒子裏的錢交學費,買作業本,也偶爾買點肉做給父親吃,是恬然的安靜感覺。這樣的日子讓人有種慣性的依賴,像一隻鳥的飛翔,沒有轉彎和阻隔。
突然的一天,父親拖着壞了很多處的車子從廢品站回來,臉上青一塊紫一塊的,透着強烈的委屈和惶惑。錢被鎮上的小混混搶了,父親被打了。我安慰了他半天,最後還是忍不住哭了。這是第一次,然後是,接二連三。父親越來越惶惑不安,吃飯越來越少,睡覺也很不安穩,經常半夜起來對着窗戶呆呆地坐幾個時辰。話也不說了,更不笑,臉上眼睜睜地消瘦下來,眼神是不安的遊移。我不知道該怎麼辦。我知道他往日細緩如流水的生活突然碰上了巨巖,他緩不過神來,難受得緊。
那天,父親去廢品站很晚了還沒回來。外面一片漆黑,心裏一陣陣發毛的我跑出去沿路找。嗓子喊破了,像一面破鑼,震得自己心裏腦裏嗡嗡的,卻並沒傳出多大響聲。夜裏的村野風吹草驚,自己的腳步聲和喊聲總會引來一片陌生的聲音。我毛骨悚然。最終在一個大水灣邊看到父親的車子,沒有人。我立刻就大哭起來,感覺整個人都化成了水在不斷地往外流,直到整個人都空了。
猛然聽到一陣急促水聲的時候,我嚇了一跳,哭聲被硬生生截斷在喉嚨裏。我望着聲音的來處,好久纔看清楚有一個人從水裏走過來,越來越近,像從水裏長出來的一樣,水被擦出一片嘩嘩聲,有沉重的呼吸聲,近了,又近了——是父親,是父親!
父親跑過來喘着氣抱住我,急急地問:“我得活着跟你做伴,對不對?”
我使勁地點頭,嗚咽不已。父親立刻笑了,像發現了真理似地說:“怎麼樣我也不能死,我得活着跟你做伴。”說完就不理不顧地牽着我回家了。
一路上他莫名的興奮對比着我的淚水。那一年我13歲,父親43。這是我生命中最銘心刻骨的一段回憶。
父親最終也沒有去把那架車子撿回來。他不再去鎮上了,就在四周圍轉,誰家田裏有草就幫忙拔,有什麼活就幫忙幹。只是每天都樂呵呵的。再後來,父親跟着村裏的一個民工小組去趕零工。他只扔磚頭,從房底扔到房上,要恰恰扔到瓦匠手上,要快,要一時不停。他的胳膊紅腫了起來,每天回來我就用熱毛巾給他敷,但不很管用,後來學習家務一忙起來,也便放棄了。有時候夜裏醒來聽到父親睡夢中沉沉的呻吟,心就一抖一抖地疼,淚流了一臉也不敢哭出聲來。父親很賣力氣,對工錢也沒有概念,給多少是多少,好在別人不太忍心欺他。
生活再一次進入正軌,我可以不用踩小凳子炒菜了,幹活也利落了許多,不再需要父親燒火了。他便轉移了目標,每天我寫作業的時候就撫一撫我的英漢大詞典,咕噥幾句“小閨女不簡單,能看這麼大的外國書”,臉上是羨慕和驕傲。我對他笑一笑,他就很歡喜地走了。父親顯然對自己過的日子心滿意足,眉眼間都活絡了許多。
高中我沒住校,仍然延續着這種生活,但是日子一天天逼近高考,我開始發慌[]。
我試探着問他:“我要到很遠的地方唸書了,你怎麼辦呢?”
“有多遠?是不是有毛主席那麼遠?”他瞪大眼睛,臉上有我看不出來的表情。我侷促地點了下頭。他竟然很高興:“閨女能到毛主席那裏去了,不簡單,我,我在家裏等你回來。”表情甚是雀躍。我不想把話題往深裏引了,怕他難受,說:“你要幹活呢。”他說:“好,幹活。”
就這樣我半頭半尾、模糊不清地完成了離別的可能,卻沒有想到在上路之前的晚上,父親變了卦,死活要送我去上學。他說,太遠了就走丟了,說得切切真情,我沒有辦法說不,就這樣拖拖拉拉出了門。
半天的汽車,一天一夜的火車。父親一直興奮着,他從來沒見過這麼多的人、這麼大的車。下車之後更不得了,他被那麼高的樓晃得頭暈,自始至終只說一句話,“神仙一樣的咧?”
我始終小心謹慎地買票、轉車、照看行李包裹、照看父親,心裏竟有種不可思議的平靜,感覺竟像我在送父親上學。
到了學校天就黑了下來,招待所父親不住,說,他在哪裏都睡得着,可不能過神仙一樣的生活呢。宿舍要關大門了,我被父親塞進去。一夜無眠,一大早就在門裏等着開門,而父親,等在門外。拉開門的一剎,我看到他滿身的泥灰,臉上也黑漆漆的,正朝門裏緊張地張望,生怕我進了那扇門他就再也見不到了似的。我趕緊迎出去,問他怎麼弄成了這個樣子。
他說,沒什麼事呀,就是夜裏冷了,看不見東西就隨手扯了塊布裹在身上。天哪,那一定是前面樓施工扔下的水泥袋子,上面是沒倒乾淨的灰粉。已經是9月的天氣了,一定冷得難當。我看着一臉是笑的父親,深吸了一口氣,仍是說不出話來。
學校招生處還沒有上班。我揣着戶口本在偌大的校園裏轉,滿是四處無依、漂泊不定的感覺,心裏很不踏實。但想到畢竟以後4年都要在這裏生活了,總有點殷殷的期望。而父親沒有,一切對他來說是那麼生疏,而生疏使他更顯侷促。在三四千裏以外的異地,他聽不懂別人說話,別人也聽不懂他。他打心底裏恐慌,一着急,就脫口而出:“我回家吧,我想回去了。”
我拗不過他,只好送他去車站。這一年我19歲,帶着年輕的夢想和莫名的迷惘進入了城市;父親49,在城市的一角作驚鴻一瞥,然後帶着滿心的喜悅,穿着又髒又破的衣服離開了。“轉身成背影了,話,怎麼說呢?”無語凝咽。
這是我跟父親惟一的一次離別,一別至今。
爲了賺取自己的學費,我每個假期都不得不留在這座城市打工。轉眼,便是4年了。父親在家望眼欲穿。我只在過節的時候把電話打到鄰居家去,父親跑來接,每次接的時候都是喜悅的,卻不知道說什麼好,就絮絮叨叨說誰家又給了他什麼吃,誰家又蓋房子他去幫工。我在這一頭捂住話筒抽泣,然後調整聲音要求他晚上給自己做點好吃的。他會答應了回去做,很認真。我羨慕父親可以用如此簡單的方式表達他的珍惜,而我總是忍不住洶涌又愚笨地欲蓋彌彰。
今天,父親的小閨女長大了,她已經學會穿着職業裝在城市的人流中匆忙行走。一個月後,領到第一筆工資的我,就可以回家看父親了。
我們曾約定過,要一輩子陪伴的。
三、《來世,別讓我這麼晚說愛你》
我盯着徐永看了好久,我對自己說,我爸就是這個樣子的,下回再遇到,不許我嫌棄他的窮,嫌棄他的沒本事,更不許嫌棄他沒血性。
(一)
我6歲的時候,徐永是一個工廠的工人,還兼了一個不當權的小幹部。那會兒,徐永是能拿得出手的,所以,我總願拉着他去街上買文具,或着拉着他去替我開家長會。那會兒,總有人會問徐永,你兒子怎麼跟你一點都不像呀,徐永總會樂呵呵的說,他像他媽,他像他媽。
那會兒,我很是忌諱別人說我和徐永長得不像,不過說到底,他是我爸,還是個芝麻官,我覺得挺有面子的。
後來,我總以爲徐永會像我夢想的那樣仕途順暢,最終作了大官,我最終成了大官的兒子,還是個芝麻官,我覺得挺有面子。
我十六歲的時候,徐永終於光榮下崗在街上開起了摩的,就是那種機動的小三輪車,載人的,一人一元。徐永很悲壯地說,一大廠子那麼多人,我不下崗誰下崗?
徐永開摩的,開得灰頭土臉,可他卻很開心。我卻有些開心不起來,畢竟,我爸是開摩的的,這說出去很不體面。
每天,徐永收工的時候,我和我媽兩個門衛,一邊一個。別誤會,我們不是迎接徐永,我們是在監督徐永把身上的髒衣服脫下來,拍拍頭上身上的土纔可以進門。徐永總是笑呵呵地毫無異議。
那時候,我瞧不起徐永,不僅僅因爲這件事情,還有另一件事情,我從何軍那裏聽來的事。
何軍是我的哥們兒,又一次我們倆拿期末退回來的班費去喝酒,何軍喝得有些多,他將酒氣沖天的嘴巴對着我的耳朵大聲地說:"徐遙,我,我跟你說件事情,你他媽的,要對你爸好些,你他媽的不是你爸的兒子,他還對你那麼好,人家容易嗎?"
我以爲何軍只是酒後胡言亂語,不在意,可這話聽起來多少是有些不舒服的,便向我媽求證。
我媽吞吞吐吐地說,我確實不是徐永的孩子。
我躲在屋子裏鼻涕一把淚一把地哭了個昏天黑地。我媽被我哭得手足無措,徐永倒是坦然了一些,把飯菜送到我的屋裏,還和顏悅色。我將那些飯菜打翻在地,心裏說,徐永,你他媽真不是男人。
也是從那時起,我更看不起徐永了。不僅僅因爲他只是個會開摩的的沒本事的男人,而是因爲他明明知道我不是他的兒子,卻把我當親生兒子那樣去寵愛,去呵護。
(二)
大二的時候,我跟別人吵架,被紮了一刀子,出了好多的血。恰好徐永和我相同的血型,他躺在另一張牀上輸血給我的時候,不停地說,徐遙,我輸了這麼多血給你,你小子再不醒來看我怎麼收拾你。其實那會我已經醒了,可是我不敢睜眼睛,我在想,徐永呀,這回我身體裏可有你的血了,你對我好就理所當然了。我在想這些的時候,眼眶裏全是水,我怕我一睜開眼,他們全跑到我臉上去被徐永看到。
於是我就那樣靜靜地躺着,不知不覺睡着了。後來,我是咯咯的笑着醒的,護士說你這人真好玩,明明是笑着醒的,怎麼眼睛裏還有淚水呀?
護士開始給我查體溫,量血壓。我偷偷地看了一眼徐永,他睡着了,他身上的被子很快地滑了下來。我說護士小姐,你替我爸爸蓋一下被子。
護士去給徐永蓋被子的時候,我又想了剛纔做的那個夢,夢裏,我還是這麼大,夢裏徐永還能抱動我,他用鬍子扎得我到處躲,躲不開就咯咯地笑,徐永也跟着笑。
我又看了看徐永,他比我夢裏老了許多。
我找護士要了一張紙,我在紙上寫了一句話讓護士放進了徐永的口袋。那句話酸不拉唧的,就是那句:爸爸,其實我挺愛你的。
我寫這句話是有依據的,當初,我失血過多快要昏迷的時候,我特別害怕,我總感覺自己這一閉上眼就蹬腿走人了。那時候我第一個想到的人竟然是徐永,第二個纔是我媽媽。我想我對不起徐永呀,我咋這麼背呢,連跟他說句對不起的機會都沒有。後來我便什麼也不知道了,好在徐永的那些血又讓我醒來了。我在心裏跟徐永開玩笑地說,我說徐永你挺自私呀,爲了讓我說聲對不起就讓自己白流了那麼多血?你笨呀徐永。可我偏不說對不起。
後來,在醫院的那些日子,我用徐永醒着的時間睡覺,用徐永睡覺的時間醒着,有時候睡不着也得睡,還裝着睡得很香。因爲那樣的時候,徐永總會給我來幾句真情告白。那感覺溫暖得不像樣子。比如徐永總說徐遙呀,別說你是你媽和別人生的,就是你媽撿來的兒子也是我徐永的。再或者,他會說,徐遙,你小子下回可別再亂鬧了,我還指望着你給我養老送終呢。
徐永這樣說着的時候,我便在心裏狠狠發誓,以後一定要飛黃騰達,給徐永些好日子過。可是,徐永的願望,我卻只完成了一半,我沒能養他的老,卻爲他送了終。
(三)
那是我大學畢業的第二個夏天,徐永還開摩的,一個雨天,他硬是沒煞住車,連人帶車掉進了城邊的河裏。當時天黑,又下着雨,所以看到這一幕的人並不多,找到的兩個目擊證人回憶說他掉下去被車扣在了下面,然後他掙扎着撲騰到水面上不住地喊救人,救人,那會兒他好像是踩在車架上,頭剛剛伸出水面,但等到我們找到會游泳的人下水救他的時候,卻找不到人了。另一個人補充說,他正喊叫着好像想起了什麼,又鑽到水下面去了,看樣子,好像到車裏拿什麼很重要的東西。
這些話後來被很多人重複,可是它們已經失去了所有的意義。徐永走了,他手裏攥着我買給他的那個太陽鏡。
那天,我趕到事發現場時,徐永平平整整地躺在河岸上,他不像是掉到河裏了,他像是在那裏睡着了結果被雨淋得溼透了。110和120還有圍觀羣衆裏三圈外三圈地把徐永圍在了中間,徐永一輩子也沒那樣輝煌過。
我走過去,拍了他兩下,我說爸,咱回家。聽到這句話的人都掉了眼淚,我也想放開聲大哭一場,可是我哭不出來。我背起徐永一步一步地往前走着,120的急救人員看不過去,好幾次勸說我把徐永放到車上去,我知道我一旦把徐永交給他們就再也要不回來了。
我本來想把他揹回家,給他換一身乾淨的衣服,再把電熱毯開上,讓他暖和一下,可能就自己醒來了。可我媽不同意,她硬是一把鼻涕一把淚地勸說我把徐永背進了醫院。
醫護人員忙碌了一番後,終於將徐永放在單車上推進了那個冰冷的空間,走廊那麼短,徐永一轉眼不見了。我跪在地上,瘋了似的叫着爸,爸爸。明知道徐永離我並不遙遠,可他充耳不聞。
那天夜裏雨很大,我把我媽送回家,又一個人去了醫院旁邊的那條街,那條街和太平間只有一牆之隔。我抽了一夜的煙,跟徐永說了一輩子最多的一回話。
天亮的時候,我媽將電話打在了我的手機上說,她也一夜未眠。她說徐遙呀,我想有件事情必須告訴你,其實我是在懷上你之後才和你爸爸結婚的,事後我告訴了他,他也不計較,而且他還去做了絕育手術。她說徐遙,上回你問我的時候,我只是簡單承認了,你知道作爲媽媽,跟你詳細交代這樣的事情,我沒有勇氣,可是這是事實。
我悄無聲息地掛了我媽的電話,我對着太平間那面被雨水淋得像血一樣鮮紅的磚牆說,爸。對不起,我愛你。
(四)
三天後,我捧着徐永的骨灰去了墓地,親手將它安葬。徐永在那隻水晶盒子上睡得很平靜,安祥。徐永臨走時我已經爲他換上了乾淨的衣服,美容師也給他整了妝。我知道徐永可能不太適應這些,可徐永這輩子爲我們娘倆風裏來,雨裏去,受了很多苦,我想讓他去另一個世界的時候,風光體面些,別再讓別人看不起他。
至於我,我會把徐永的樣子刻進骨頭裏,下回我們父子再相遇,無論他貧富是否,我都不會嫌棄他的窮,他的沒本事,不會埋怨他的沒血性,更不會那麼晚告訴他,爸爸,我真的愛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