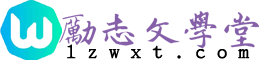簡短感人的母愛的小故事
簡短感人的母愛的小故事

導語:人的嘴脣所能發出的最甜美的字眼,就是母親,最美好的呼喚,就是“媽媽”。這裏本站的小編爲大家整理了三篇簡短感人的母愛的小故事,希望你們喜歡。

故事一:《你的眼淚是一條河》
母親哭了,在搖曳的光影裏。60年了,多少苦澀的淚伴着逝去的歲月,在母親的臉上流呀流,流走了母親滿頭的青絲,流成了道道細密的小河。母親是個苦命的人,她13歲那年夏天,我外婆突然中風去世了,母親在外婆的墳前哭幹了最後一滴眼淚,就擔起了操持家務照料妹妹的擔子。默默勞作、不善言談的性格便是從那時候養成的。日子的艱難、心中的愁苦,無人傾訴,只有在夜裏默默流淚。
母親20歲那年冬天,嫁到了我們李家,我的父親小母親一歲,家境雖很貧寒,可在十里八村,父親稱得上是一個出色的小夥子。貧家女是不怕過窮日子的,只要她的心能有個依靠就夠了。哪承想婚後不久,父親就因勞累過度患了肺病,時常大口大口地吐血,母親流着淚,求父親去治療,執拗剛烈的父親卻咬牙發誓不把日子過好,他死也不去治病。母親知道父親的心思,他是怕花錢。看着四壁如洗的兩間土坯西廂房,家裏也真拿不出錢來給父親治病,母親除了拼死幹活兒來減輕父親的勞累,就是終日含淚祈求老天保佑。不知是不是母親虔誠的禱告感動了上蒼,半年後,父親的病竟然不治自愈了,三間新房也蓋了起來。房子蓋好的那天,母親抱着父親大哭了一場。
日子稍稍好過一點的時候,我來到了世上,從出生那一天起就把無盡的牽掛與愁苦帶給了她,母親的生命從此成爲一支被我點燃的蠟燭,再沒有停止過燃燒和流淚。
不滿一歲的時候,我得了急性腸炎,這病在三十多年前的農村,是可以置人於死命的。當時,已經擔任村支部書記的父親遠在幾百裏外的地委黨校學習,母親抱着氣息奄奄的我,衝進雷電交加的茫茫雨夜,一路跌跌撞撞,終於在子夜敲開了十里外一個老中醫的家門。母親跪在老中醫的面前,求他救救她的兒子,她再次用她的淚感動了上蒼,我竟死裏逃生,奇蹟般地活了下來。
說起來,我還 算給母親爭氣,從小學到中學一路讀過來,沒讓她失望。1980年,18歲的我參加高考竟考了個全縣文科第一,母親連夜把我的被子拆了添絮了一層新棉,燈光下,她手中的針線起起落落,點點滴滴的淚水連同那顆慈母心都絮進了那厚厚的棉被裏。
大學畢業後,我被分到一個新興城市工作,母親沒再做太多的囑咐,只對我說:“你真的長大了,以後出門在外,要行善事,做好人。媽在家等你回來過年團圓。”可是,母親盼來的不是兒子歸來的團圓,而是我患病住院的音訊。已是農曆臘月中旬,單位的車把父母接到我所住的醫院,母親踉蹌着撲到我的牀頭,抱着我的頭,泉涌般的淚水潤溼了我的臉。我的心裏滿是對母親深深的歉意,爲什麼我帶給你的總是流不盡的淚?我真是一個不懷好意的討債鬼嗎?
在以後整整18個月的日子裏,病魔與死神將我這個不滿24歲的生命當成它們手中的一根扯來扯去的猴皮筋,母親用她帶血的淚水和根根白髮陪着我一道跟它們較量,最終我竟奇蹟般擺脫了死神的糾纏,可是它沒有空手而去,挖走了我的一雙眼睛。
那是一個飄着細雨的暮春之夜,病房裏很安靜,母親小聲對我說:“你要是難受就抽支菸吧。這是我從小賣部給你買來的,是你從前愛吸的‘大前門’牌,護士都查過房了,不會有人來了。”母親的話怯生生的。對沒了眼睛的兒子,已是心碎的母親,猶如做錯了事的孩子,不知如何才能不惹我發怒。
黑暗中,我下意識地伸出手,她竟看見了,忙把一支菸放到我手中,然後又急急忙忙地去找火柴。我深吸一口久違的香菸,許久才伴着一聲重重的嘆息吐出濃濃的煙霧,母親又小心翼翼地開口了,“媽知道你心裏難受,可我們總還 得活下去活,像我這樣活着有啥用?”這是我幾個月來第一次順着母親的話茬答言,母親受到更大的鼓勵,咋沒用,只要你還 活着,只要我和你爹下地回來能看到牀上坐着他們的兒子,我們心裏就踏實,就有奔頭窗外的雨下得大了,落在長出新芽的樹上沙沙作響,忽覺得臉上癢癢的用手去摸,是淚。
肆虐的風暴過去了,生命之樹帶着累累傷痕終又艱難地站了起來。在家休養了三年後,我又鼓起勇氣上路了,因爲有母親那句:“咱要好好活!”我必須走出一條活的路來。幾年來我的腳下已有一條路的雛形,儘管還 不是很清晰,儘管還 很狹窄,但那是我自已用腳踩出來的,是我活着的見證,這條路上有我的夢,也有母親的淚。如果說我的生命是一條船,那麼母親的眼淚就是一條河了。四年前一場婚變,又在母親含着眼淚默默地擔起了撫養我六歲幼兒的責任。
母親啊,你的眼淚真是一條流不盡的河,每當我的生命之船擱淺了,你總是用自已的生命托起我這隻船,送我到遠方。
故事二:《從狼嘴裏換來的母愛》
那是19年前的事了。
那時我9歲,同母親住在川南那座叫茶子山的山腳下。父親遠在省外一家兵工廠上班。
母親長着一副高大結實的身板和一雙像男人一樣打着厚繭的手,這雙手只有在託着我的腦袋瓜子送我上學或拍着我的後背撫我人睡的時候,我才能感覺到她的不可抗拒的母性的溫柔與細膩。除此之外,連我也很難認同母親是個純粹的女人,特別是她揮刀砍柴的動作猶如一個左衝右突威猛無比的勇敢戰將,砍刀閃着灼人的寒光在她的手中呼呼作響,粗如手臂的樹枝如敗兵一般在刀光劍影下嘩嘩倒地。那時的我雖然幼小,但已不欣賞母親這種毫無女人味的揮刀動作。在那個有雪的冬夜,在那個與狼對峙的冬夜,我對母親的所有看法在那場驚心動魄的“戰爭”後全然改寫。學校在離我家6裏處的一個山坳裏,我上學必須經過茶子山裏一個叫烏託嶺的地方,烏託嶺方圓2裏無人煙,嶺上長着並不高大的樹木和一叢叢常青的灌木。每天上學放學,母親把我送過烏託嶺然後又步行過烏託嶺把我接回來。接送我的時候,母親身上總帶着那把砍柴用的砍刀,這並非是怕遇到劫匪,而是烏託嶺上有狼。1980年冬的一個週末,下午放學後,因我肆無忌憚的玩耍而忘掉了時間,直到母親找到學校,把我和幾個同學從一個草垛裏揪出來我才發現天色已晚。當我隨母親走到烏託嶺的時候,月亮已經升起在我們的頭頂。
這是冬季裏少有的一個月夜。銀色的月光傾瀉在叢林和亂石間,四周如積雪一般一片明晃晃的白。夜鶯藏在林子深處一會兒便發出一聲悠長的啼叫,叫聲久久地迴盪在空曠的山野裏,給原本應該美好的月夜平添了幾分恐怖的氣崽。
我緊緊地拉着母親的手,生怕在這個前不挨村後不着店的鬼地方遇到從未親眼目睹過的狼。狼在這時候真的出現了。
在烏託嶺上的那片開闊地,兩對狼眼閃着熒熒的綠光,彷彿四團忽明忽暗的磷火從一塊石頭上冒了出來。我和母親幾乎是在同時發現了那四團令人恐懼的綠光,母親立即伸手捂住我的嘴,怕我叫出聲來。我們站在原地,緊盯着兩匹狼一前一後慢慢地向我們靠近。那是兩隻飢餓的狼,確切地說是一隻母狼和一隻尚幼的狼崽,在月光的照映下能明顯地看出它們的肚子如兩片風乾的豬皮緊緊貼在一起石母親一把將我攬進懷裏,我們都屏住了呼吸,眼看着一大一小兩條狼大搖大擺地向我們逼近,在離我們6米開外的地方,母狼停了下來,冒着綠火的雙眼直直地盯着我們。
母狼豎起了身上的毛,做出騰躍的姿勢,隨時準備着撲向我們。狼崽也慢慢地從母狼身後走了上來,和它母親站成一排,做出與母親相同的姿勢,它是要將我們當作訓練捕食的目標!慘淡的月光。夜鶯停止了啼叫。沒有風,一切都在這時候屏聲靜氣,空氣彷彿已凝固,讓人窒息得難受。
我的身體不由地顫抖起來,母親用左手緊緊攬着我的肩,我側着頭,用畏懼的雙眼盯着那兩隻將要進攻的狼。隔着厚厚的棉襖,我甚至能感覺到從母親手心浸人我肩膀的汗的潮潤。我的右耳緊貼着母親的胸口,我能清晰地聽見她心中不斷擂動着的狂烈急速的“鼓點”。然而母親面部表情卻是出奇的穩重與鎮定,她輕輕地將我的頭朝外挪了挪,悄悄地伸出右手慢慢地從腋窩下抽出那把尺餘長的砍刀。砍刀因常年的磨礪而閃爍着懾人的寒光,在抽出刀的一剎那,柔美的月光突地聚集在上面,隨刀的移動,光在冰冷地翻滾跳躍。
殺氣頓時凝聚在了鋒利的刀口之上。也許是懾於砍刀逼人的寒光,兩隻狼迅速地朝後面退了幾步,然後前腿趴下,身體彎成一個弓狀。我緊張地咬住了自己的嘴脣,我聽母親說過,那是狼在進攻前的最後一個姿勢。
母親將刀高舉在了空中,一旦狼撲將上來,她會像砍柴一樣毫不猶豫地橫空劈下!那是怎樣的時刻啊!雙方都在靜默中作着戰前較量,我彷彿聽見刀砍人狼體的“撲詠”的悶響,彷彿看見手起刀落時一股狼血噴面而來,彷彿一股濃濃的血腥已在我的嗅覺深處瀰漫開來。
母親高舉的右手在微微地顫抖着,顫抖的手使得刀不停地搖晃,刺目的寒光一道道飛彈而出。這種正常的自衛姿態居然成了一種對狼的挑釁,一種戰鬥的召喚[]。母狼終於長嗥一聲,突地騰空而起,身子在空中劃了一道長長的弧線向我們直撲而來。在這緊急關頭,母親本能地將我朝後一撥,同時一刀斜砍下去。沒想到狡猾的母狼卻是虛晃一招,它安全地落在離母親兩米遠的地方。刀沒能砍中它,它在落地的一瞬快速地朝後退了幾米,又作出進攻的姿勢。
就在母親還 未來得及重新揮刀的間隙,狼惠像得到了母親的旨意緊跟着飛騰而出撲向母親,母親打了個趔趄,跌坐在地上,狼崽正好壓在了母親的胸上。在狼崽張嘴咬向母親脖子的一剎,只見母親伸出左臂,死死地扼住了狼崽的頭部。由於狼崽太小,力氣不及母親,它被扼住的頭怎麼也動彈不得,四隻腳不停地在母親的胸上狂抓亂舞,棉襖內的棉花一會兒便一團團地被抓了出來。母親一邊同狼崽掙扎,一邊重新舉起了刀。她幾乎還 來不及向狼崽的脖子上抹去,最可怕的一幕又發生了。
就在母親同狼崽掙扎的當兒,母狼避開母親手上砍刀折射出的光芒,換了一個方向朝躲在母親身後的我撲了過來。我驚恐地大叫一聲倒在地上用雙手抱住頭緊緊地閉上了眼睛。我的頭腦一片空白,只感覺到母狼有力的前爪已按在我的胸上和肩上,狼口噴出的熱熱的腥味已經鑽進了我的領窩。也就在這一刻,母親忽然悲槍地大吼一聲,將砍刀埋進了狼崽後頸的皮肉裏,刀割進皮肉的刺痛讓狼崽也發出了一聲渴望救援的哀嚎。奇蹟在這時發生了。
我突然感到母狼噴着腥味的口猛地離開了我的頸窩。它沒有對我下口。我慢慢地睜開雙眼,看到仍壓着我雙肩的母狼正側着頭用噴着綠火的眼睛緊盯着母親和小狼崽。母親和狼崽也用一種絕望的眼神盯着我和母狼。母親手中的砍刀仍緊貼着狼崽的後頸,她沒有用力割人,砍刀露出的部分,有一條像墨線一樣的細細的東西緩緩地流動,那是狼崽的血!母親用憤怒恐懼而又絕望的眼神直視着母狼,她緊咬着牙,不斷地喘着粗氣,那種無以表達的神情卻似最有力的警告直逼母狼:母狼一旦出口傷害我,母親就毫不猶豫地割下狼崽的頭!動物與人的母性的較量在無助的曠野中又開始久久地持續起來。無論誰先動口或動手,迎來的都將是失子的慘烈代價。相峙足足持續了5分鐘母狼伸長舌頭,扭過頭看了我一眼,然後輕輕地放開那隻抓住我手臂的右爪,繼而又將按在我胸上的那隻左腳也抽了回去先前還 高聳着的狼毛慢慢地趴了下去,它站在我的面前,一邊大口大口地喘氣,一邊用一種奇特的眼神望着母親母親的刀慢慢地從狼惠脖子上滑了下來,她就着臂力將狼崽使勁往遠處一拋,“撲”地一聲將它拋到幾米外的草叢裏。母狼撒腿奔了過去,對着狼崽一邊聞一邊舔。母親也急忙轉身,將已嚇得不能站立的我扶了起來,把我攬人懷中,她仍將砍刀緊握在手,預防狼的再一次攻擊。
母狼沒有做第二次進攻,它和狼崽佇立在原地呆呆地看着我們,然後張大嘴巴朝天發出一聲長嗥,像一隻溫順的家犬帶着狼崽很快消失在幽暗的叢林中。
母親將我背在背上,一隻手託着我的屁股,一隻手提着刀飛快地朝家跑去,剛邁進家門檻,她便腿一軟摔倒在地昏了過去,手中的砍刀“吮當”一聲摔出好幾米遠,而她那像男人般打滿老繭的大手仍死死地摟着還 趴在她背上的我。
故事三:《三袋米中的母愛》
這是一個真實的故事。這是個特困家庭。兒子剛上小學時,父親去世了。孃兒倆相互攙扶着,用一堆黃土輕輕送走了父親。
母親沒改嫁,含辛茹苦地拉扯着兒子。那時村裏沒通電,兒子每晚在油燈下書聲朗朗、寫寫畫畫,母親拿着針線,輕輕、細細地將母愛密密縫進兒子的衣衫。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當一張張獎狀覆蓋了兩面斑駁陸離的土牆時,兒子也像春天的翠竹,噌噌地往上長。望着高出自己半頭的兒子,母親眼角的皺紋張滿了笑意。
當滿山的樹木泛出秋意時,兒子考上了縣重點一中。母親卻患上了嚴重的風溼病,幹不了農活,有時連飯都吃不飽。那時的一中,學生每月都得帶30斤米交給食堂。兒知道母親拿不出,便說:“娘,我要退學,幫你幹農活。”母親摸着兒的頭,疼愛地說:“你有這份心,娘打心眼兒裏高興,但書是非讀不可。放心,娘生你,就有法子養你。你先到學校報名,我隨後就送米去。”兒固執地說不,母親說快去,兒還 是說不,母親揮起粗糙的巴掌,結實地甩在兒臉上,這是16歲的兒第一次捱打……
兒終於上學去了,望着他遠去的背影,母親在默默沉思。
沒多久,縣一中的大食堂迎來了姍姍來遲的母親,她一瘸一拐地挪進門,氣喘吁吁地從肩上卸下一袋米。負責掌秤登記的熊師傅打開袋口,抓起一把米看了看,眉頭就鎖緊了,說:“你們這些做家長的,總喜歡佔點小便宜。你看看,這裏有早稻、中稻、晚稻,還 有細米,簡直把我們食堂當雜米桶了。”這位母親臊紅了臉,連說對不起。熊師傅見狀,沒再說什麼,收了。母親又掏出一個小布包,說:“大師傅,這是5元錢,我兒子這個月的生活費,麻煩您轉給他。”熊師傅接過去,搖了搖,裏面的硬幣丁丁當當。他開玩笑說:“怎麼,你在街上賣茶葉蛋?”母親的臉又紅了,支吾着道個謝,一瘸一拐地走了。
又一個月初,這位母親揹着一袋米走進食堂。熊師傅照例開袋看米,眉頭又鎖緊,還 是雜色米。他想,是不是上次沒給這位母親交待清楚,便一字一頓地對她說:“不管什麼米,我們都收。但品種要分開,千萬不能混在一起,否則沒法煮,煮出的飯也是夾生的。下次還 這樣,我就不收了。”母親有些惶恐地請求道:“大師傅,我家的米都是這樣的,怎麼辦?”熊師傅哭笑不得,反問道:“你家一畝田能種出百樣米?真好笑。”遭此搶白,母親不敢吱聲,熊師傅也不再理她。
第三個月初,母親又來了,熊師傅一看米,勃然大怒,用幾乎失去理智的語氣,毛辣辣地呵斥:“哎,我說你這個做媽的,怎麼頑固不化呀?咋還 是雜色米呢?你呀,今天是怎麼背來的,還 是怎樣揹回去!”
母親似乎早有預料,雙膝一彎,跪在熊師傅面前,兩行熱淚順着凹陷無神的眼眶涌出:“大師傅,我跟您實說了吧,這米是我討……討飯得來的啊!”熊師傅大吃一驚,眼睛瞪得溜圓,半晌說不出話。
母親坐在地上,挽起褲腿,露出一雙僵硬變形的腿,腫大成梭形……母親抹了一把淚,說:我得了晚期風溼病,連走路都困難,更甭說種田了。兒子懂事,要退學幫,被我一巴掌打到了學校她又向熊師傅解釋,她一直瞞着鄉親,更怕兒知道傷了他的自尊心。每天天矇矇亮,她就揣着空米袋,拄着棍子悄悄到十多裏外的村子去討飯,然後捱到天黑後才偷偷摸進村。她將討來的米聚在一起,月初送到學校……母親絮絮叨叨地說着,熊師傅早已潸然淚下。他扶起母親,說:“好媽媽啊,我馬上去告訴校長,要學校給你家捐款。”
母親慌不迭地搖着手,說:“別、別,如果兒子知道娘討飯供他上學,就毀了他的自尊心。影響他讀書可不好。大師傅的好意我領了,求你爲我保密,切記切記!”
母親走了,一瘸一拐。
校長最終知道了這件事,不動聲色,以特困生的名義減免了兒子三年的學費與生活費。三年後,兒子以627分的成績考進了清華大學。歡送畢業生那天,縣一中鑼鼓喧天,校長特意將母親的兒子請上主席臺,此生納悶:考了高分的同學有好幾個,爲什麼單單請我上臺呢?更令人奇怪的是,臺上還 堆着三隻鼓囊囊的蛇皮袋。此時,熊師傅上臺講了母親討米供兒上學的故事,臺下鴉雀無聲。校長指着三隻蛇皮袋,情緒激昂地說:“這就是故事中的母親討得的三袋米,這是世上用金錢買不到的糧食。下面有請這位偉大的母親上臺。”
兒子疑惑地往後看,只見熊師傅扶着母親正一步一步往臺上挪。我們不知兒子那一刻在想什麼,相信給他的那份震動絕不亞於驚濤駭浪。於是,人間最溫暖的一幕親情上演了,母子倆對視着,母親的目光暖暖的、柔柔的,一綹兒有些花白的頭髮散亂地搭在額前,兒子猛撲上前,摟住她,嚎啕大哭:娘啊,我的娘啊